她在前十天里忍着不给他发一个字的短信,就是为了避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这样他选择了她也才不能归罪于她。不然他选择了白玫瑰,终究觉得还是红玫瑰让他魂牵梦萦。选择了红玫瑰,又觉得白玫瑰才是玫瑰,自己选了红的简直就是上当了。她根本就不给他这个机会懊悔,她放任自流,让他自己选择去。可是临到头,她还是发现,另一个女人的影子阴魂不散地附在他们中间。而且她就是使尽全力都驱不走她,因为,她是看不见的。她在明处,她在暗处,她怎么能是她的对手?这种失败比当初张以平和她分手更让她撕心裂肺。
黑暗中,她更紧地抱住他,想要把那个女人驱走。她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俗不可耐的话,你爱我吗?她不用听答案就知道他会说,爱啊,不爱怎么会和你在一起。果然,他在黑暗中说,爱啊,不爱怎么会和你在一起。都没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爱怎么会在一起?她可悲地发现,她又一次陷入了被动的劣势。因为这句话的反面其实就是,不在一起的也可以是爱的。女人用假话来为自己撑腰,就像是在饥饿时喝凉水也可以产生暂时的满足感。那是一种致幻效果。而她分明已经沦落到了这种地步。现在,他抱着她,吻她,和她做爱,她却觉得他们之间就是有一层东西,只要她不戳破这层东西,他们就是面对面的时候,都是咫尺天涯的。
她必须得下手,她必须得狠得下来。即使明知道一伸手就是血淋淋的东西。她问,那你还爱她吗?他不回答,选择了可怕的沉默。这沉默比他说上成百上千句话都可怕。她的心里猛地抽搐了一下,就像是被一把刀子捅进去又搅了一番。她的声音已经开始打战了,她瑟缩着,发着抖,却还是问了一句,你还爱她,是吧。她明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她每往前走一寸就多一寸的鲜血淋漓,就多一寸的疼痛,她还是忍不住要往前走。索性就见底了,就痛到底了,看还能怎样。她终于纵容了自己的委屈,所有的委屈像包在薄薄的皮下的浆汁,立刻喷涌而出。她几乎是声嘶力竭地说了一句,你要是还爱她,为什么不和她到一起去。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也爱你。她彻底紊乱了,你到底爱谁,你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但张以平很轻易就把她打败了,他说,青提,我已经和你说过了,你和一个人分开并不等于就没有感情了,我爱你所以要和你在一起,可是这并不是说我就对她没有感情了啊,我承认我还是放不下她。我和她分手也让我觉得对不起她。
她恨不得从床上蹦起来,把床上所有这些东西扔到地上去,她恨不得把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砸光了,然后狠狠地扬长而去。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东西,你是超人吗?你居然有能力同时爱两个女人,哪个都舍不得放下。居然因为和她分手而难过?搞得她孟青提是个破坏他们感情的第三者一样,死皮赖脸地要插进来?无耻,简直是无耻至极。可是,她终究没有这样做,因为她知道一旦她那样离开,她就再不可能回到这间屋子里来了。那就真的是绝境了。她不想,原来幻想这东西,是只要有一点点空隙都会不停疯长的,都会随时长成茂密的森林。一个人要想彻底做到灰心,竟也是一件艰苦卓绝的事情。
孟青提决定改变策略。前一阵子她示软是因为她知道应该给他留空间,让他自己去想清楚。她知道把一个人往死角里逼极有可能两个人最后同归于尽。可是她所留的空间只是无限助长了这个男人的混沌和暧昧不清,他简直是想怎么长就怎么长,连一点规则都不要了。好像所有的伦理和道德都奈何不了他了,他要是有本事干脆不做地球人就上月球去。她开始施行高压手段。一看见他发短信就问给谁发的,给我看一下。如果看到他偷偷去卫生间接电话,那她顿时就醋意大发,一定要哭闹一场才肯罢休。其实她心里明白得像镜子一样,一个男人要是真想出轨,那女人又怎么能拦得住他。一个男人要是就想背地里和一个女人联系,那他什么办法想不出呢?她知道自己这些做法分明就是很愚蠢的,再愚蠢不过了。她在表面上遏制了他,其实却是在把他向更深的本质里推。可是,一旦嫉妒像毒蛇一样咬住她的脖子,她还是要身不由己地发作。似乎那毒性就藏在她身体里了。嫉妒和贪婪让人愚蠢,现在,她不仅嫉妒,还贪婪。她为什么那么恐惧他还和别的女人联系,因为她不愿意让他还爱着别人,她想让他把所有的爱都一心一意给她,无限制地宠她,疼她。这本身就是一种贪婪。所以,她活该愚蠢,活该最后死无葬身之地。
张以平有时候会回来得很晚,借口是在办公室里赶稿子了,回到家里不如在办公室里心静。他说这么多年过惯了单身生活,猛然有个人一天到晚在家里晃来晃去,他还真不适应。她想,他根本就不想让她长期待在这里,他恨不得她消失,恨不得把她毁尸灭迹才好。一天晚上到十一点了,他还没有回来。她忽然就想,他是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这个想法一旦在她脑子里出现,便立刻成燎原之势,很快就把她吞噬进去了。她这才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恶俗的三角恋,恶俗的婚姻保卫战,爱情保卫战,那些小三小四的电视连续剧何以把全中国一半的家庭主妇都吸引到了电视机前,它们果然是有市场的,因为像她这样的女人太多了。女人们需要看戏的时候一边诅咒第三者,一边把自己提升到一个理论高度上。更坚不可摧的事实是,她也是个女人。
她果断地开始打他的电话,居然是正在通话。这么说,他不是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但她本能地不放心,过了五分钟,她又打,还是占线。就这样每隔五分钟她打一次,可是每一次他的电话都是正在通话。她从十一点打到将近一点,两个小时里,她打他的电话打了三十多次。最后一个电话终于通了,她劈头就问,怎么还不回来?他居然若无其事地回答,刚在赶稿子呢,明早要上头条的,刚刚写完,累死我了。他撒谎居然撒得这样脸不红心不跳,不回家就是为了给别人打一个两个小时的电话,打完之后还要告诉她,他是加班了。
她不让他在家里打电话,那他就干脆在外面打。打得更是有恃无恐,居然说了两个小时的话,甚至更长。
她静静地把自己窝在沙发里,全身蜷曲起来,像一只临死的秋虫。他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她另一个女人的存在,于是这女人便干脆在这屋子里安了家,每天和她形影相随,寸步不离。如果再在这屋子里待下去,她就会死在这男人和女人的手里。刚才那三十多个电话已经把她榨干了,现在她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里都没有一点点力气了,她彻底地干了,枯了,见底了。她成了一池碎萍凋零之后埋在泥土中的嶙峋的残藕,满身是洞,却仍是藕断丝连。离开这里吧,离开这个男人吧。她趁着那最后一些气若游丝的活气对自己说,还是认输吧,不然真要死在他手里了。今晚就走吧,就是半夜也要走,无论坐什么交通工具,就是光脚徒步,也要走。
悲愤交集给她打了一针强心剂,她像回光返照似的从沙发上弹了起来,摸摸索索地开始找自己的东西自己的皮箱。那只皮箱空空地亘在她面前,像是她背过来的一只壳。现在,她又要背着这壳离开了。她这只跋涉千里寻找温暖的蜗牛啊,荒谬到了让人落泪。她把衣服一件件往里塞,把化妆品也往里塞,她给自己一种气势,就是一定要离开这里。可是,她为什么还是这么疼痛。她看着那些衣服上的每一道褶子,都觉得那是她自己身体上的,她怜惜着它们,就像怜惜着她自己。
她穿上风衣,围上围巾,戴上那顶血红色的礼帽,长发垂下遮住了她的半张脸。她就像一个即将登场的演员。就在这时,那扇门开了,像拉开了一道幕布,上面站的是张以平。他们两个像正身在一个折叠起来的时光容器里,踩着的是时光,头顶上是时光,四壁里也是时光。头即是尾,尾即是头,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洪荒一片中他们四目相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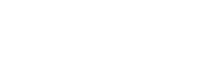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梦中未必丹青见
梦中未必丹青见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何须深情永不负
何须深情永不负 许君千万岁
许君千万岁 宛音如晏
宛音如晏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错遇
错遇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玄灵天尊
玄灵天尊 京城第一绿茶
京城第一绿茶 星河不暗淡
星河不暗淡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很少推荐小说,但《鱼吻》是我最近看的很精彩的一部。文章内容算是比较有创新的,加上孙频的创作形式很有趣,整篇文章读下来如行云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