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还有些懵的周氏刹那间回过神来了,脖颈上传来的冰凉令她不敢轻易动弹,只能吱哇乱叫:“你做什么,快放开我!意浓……意浓!你赶紧将牌位给这个疯子罢!”
何意浓未想到这一出,顿时有些气急败坏,皱着秀眉愤然道:“你竟然如此卑鄙!”
燕卿的折扇更逼近了周氏一些,只笑道:“彼此彼此。”
局面僵持不下了起来,何远德本就怯懦,这时候自然不敢出声说什么话的,只能躲在小厮后头小心张望着。而家中的护卫,也早被沈眉山带人牵制住,何意浓见无人可助自个儿一臂之力,气上心头,愤然将牌位摔在地上,恶狠狠的说道:“拿去便是!”
那牌位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燕卿脑中顿时一片空白,她根本就没有思考,直接划破了周氏的喉咙。
“娘亲!”
“夫人!”
鲜血喷涌而出,原本被燕卿挟制着还在乱叫的周氏,瞬间没了声音。
她的双眼还惊恐的睁大着,口中还剩下半句没说完的话,却也没什么机会说了。
燕卿的折扇上沾满了鲜血,她将周氏丢在地上,随后捡起娘亲的牌位,擦去上边的灰尘抱在怀中。眼中充满森森寒意,望着花容失色无比悲痛的何意浓,说道:“往后,你待我几分,我便还你几分。”
“你这个疯子,你杀人了!我要报官!”何意浓从小娇生惯养,燕卿此刻的举动,她根本不能接受,张牙舞爪地朝着燕卿扑过来。
只是才到半路,便被沈眉山拦住。
燕卿看着她崩溃的模样,忽的笑了:“你尽管去报,让我瞧瞧,谁敢接这桩案。”
她是战功赫赫的木兰将军,身后站着的,除了十万木兰军之外,还有秦如斯。
那是闳国之柱,今朝国相,圣上都要避让三分。
区区何家,能耐她何?
何意浓虽娇气,但不至于蠢笨,当中关系自然能明白。她晓得自个儿奈何不了燕卿,却又不甘心就此让步,便只能狠声说道:“何天娇,你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
“这儿哪有何天娇。”燕卿很是无辜地摊了摊手,四顾一圈,只瞧见吓得快滚过去的何远德,嗤笑一声接着说道,“本将叫燕卿,你须得记清了。”
“本将也没心思与你们耍些小手段,再弄些扮猪吃虎的名堂来,今日你们都在,便于你们说清楚。”
“恩要报,怨要偿,你们欠本将的,都得还!”
何家要还她娘亲的名声,还她所有的钱财,也得还那些无休止的怨。
这是他们种下的因,就得尝这后来的果。
何意浓的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她浑身都战栗着,看着面前陌生的人,咬牙切齿,一遍又一遍的说着:“你得意不了太久……你会遭报应的……”
“什么报应,我都替她担着。”
自何家门外,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来人清风霁月,衣袖上不带凡间尘灰,眉目清冷,踏进了院中。
燕卿抬起头来,无论多少次,秦如斯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都能让她赞叹一声凡中仙。他是昏暗天地间迟来的白昼,也是她命中千缠万痴的红线。
秦如斯瞧见这一地狼藉,什么都没说,眼神越过众人,稳稳当当地落在燕卿身上,不容抗拒的说:“过来。”
南征北战的日子里,燕卿何曾惧怕过谁?在战场上,最不能有的,就是怕。
可是此刻,她竟甘心臣于秦如斯身畔。
没有人敢阻拦,只瞧着燕卿一步一步走向了秦如斯。
何意浓与燕卿插肩而过的时候,才感受到了她身上凌冽的杀意,一时无法站立,瘫软在地。
她双目盈泪,万分娇弱的看向秦如斯,摆出些可怜模样来,率先告起了状:“传言秦相办事最为公正,从不偏私,今日之事敢问秦相如何收尾?”
“今日,发生什么事了吗?”秦如斯故作不解,仿佛没瞧见大堂里周氏的尸身跟满地的鲜血,只无辜的说,“我并未看到。”
何意浓顿时气结,胸口剧烈起伏着,却还要装模作样地哭诉:“秦相既然不知,那小女便一一说与你听。我们何家与燕将军无冤无仇,燕将军却滥用职权,杀我娘亲,扰我何家祠堂,这该当何罪?”
秦如斯耐着性子听完了,却在听完之后,侧过头去问燕卿:“你真做了这些事儿?”
燕卿一时间不晓得秦如斯这是玩哪出,做没做不都摆在眼前么?从前可没听人说过大名鼎鼎的秦相耳背啊?
既然琢磨不出来,那便不去琢磨。燕卿绝非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此刻点了点头,坦率说道:“是我做的。”
秦如斯闻言点了点头,正当众人都以为秦相要出来主持公道时,却听他格外淡然而肯定的与何意浓说:“听见了吗?她说这不是她做的。”
此刻,在场的人都以为自个儿耳朵出了毛病。
方才燕将军,好像不是这般说得罢……
何意浓最为茫然,短短半日就发生了如此多变故,让她有些回不过神来。
最终,还是沈眉山没忍住笑出声,才打破了这诡异的安静。
燕卿的耳根子有些烧红,可秦如斯还是淡定自如的模样,好似他方才并没有撒谎。她倒是从未想到,素来正经的秦相,还会耍这点小手段。
瘫软在地上的何意浓总算是回过神来了,她一时间有些恼怒,但在秦如斯面前却不太敢发作,只能忍气吞声的辩解着:“秦相,你这样做不大妥当……”
“有什么不妥当的?”秦如斯执起燕卿的手,说道,“我妻说她没做过,那便是没做过,这天底下谁不信她,我都要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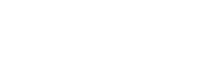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爱的一千零一次谎言
爱的一千零一次谎言 太监武帝:功法自动大圆满!
太监武帝:功法自动大圆满! 穿越成了世子的丫鬟
穿越成了世子的丫鬟 穿成恋爱脑女主后妈,我先撕为敬!
穿成恋爱脑女主后妈,我先撕为敬! 只此情深
只此情深 周凌峰廖丽珍
周凌峰廖丽珍 真心不可鉴
真心不可鉴 逆天BUG!开局触发SSS级魅魔倒追
逆天BUG!开局触发SSS级魅魔倒追 高冷室友喝催乳剂生下宝宝
高冷室友喝催乳剂生下宝宝 我叫叶玄是一个穿越者
我叫叶玄是一个穿越者 王子陵你敢跟我离婚
王子陵你敢跟我离婚 我跟十年闺蜜决裂了
我跟十年闺蜜决裂了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逆凰》的文笔有些小浪漫,有些文字真的值得研究和收藏,仔细阅读之后会回味无穷。已经被关山子规成功圈粉,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