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坤想起来看个究竟,但由于意识很朦胧慢慢地又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很沉,醒来后发现米君超不见了,只留下了那面小红旗。
阿坤反复琢磨着夜里看到的情景,知道那不是自己在做梦,也没跟冯亮说,两天后冯亮在小树洞里找到了第二面红旗,于是顺着记号,互相搀扶着下了山。
到了河岸边,俩人趴在地上,把头侵入河中,又慢慢抬头,翻身躺在岸上,手里抓着红旗来回摇摆,嗓音已经嘶哑,但还在尽情的呼喊着。
河对面就是接他们两个回营地的汽车。考官靠在车门上,脸上挂着一丝难得的微笑。
米君超死亡的消息传开了,一直在暗处的救援队说米君超晚上对着空气说话,然后就晃晃悠悠的在山上来回转了几个小时,他们一直跟着米君超,直到他倒下时才发现米君超已经严重休克,没有抢救过来,属于意外死亡。
阿坤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这儿事,免的别人说他迷信思想严重。
我俩聊得正起劲,一个黑影站在胡同拐角处,背对着我们一动不动,嘴里还哼着小曲儿。
阿坤用手电筒照过去,那人身上一阵哆嗦转过身来,由于光线太强,他一只手挡住脸,另一只手正在慌忙紧着裤腰上的烂布条腰带。
他弯着腰,脖子伸的大长,对我和阿坤吼道:“谁呀!撒泡尿也不让安生。”
阿坤关了手电掏出一支烟,又打开手电对那人招呼了一句:“哎!借个火用一下。”
那人一听,得意地又蹦又跳走到我俩身旁,一脸奸笑道:“二位这是打哪来啊!大半夜的蹲在这里守啥呢?”
说着从烂大衣口袋里拿出火柴,阿坤掏出一支烟叼在嘴里,他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阿坤嘴里的烟不放。
阿坤嘴角扬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有这玩意儿。”
阿坤伸手把火柴夺了过来,又递给他一支烟。
他急忙接过,跟捡了宝贝似得双手捧着香烟放在鼻子上闻了闻,点上烟嘿嘿一笑,露出一嘴大黑牙。
这人看样子四十来岁,满脸奸相,蹲在我俩旁边猛地的抽了一口说道:“我叫水多余,外人都叫我水子,瞅着两位不像是本地人啊!是不是想来这里做点小生意,有啥需要帮忙的尽管打声招呼。”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他想从我和阿坤这里捞点油儿头。
我微笑道:“我们是简滨的,来这里办点事儿,呆不长的,对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挺邪门儿的,我俩在这里转了大半个晚上也出不去。”
水多余犹豫一下说:“这里跟城里比起来就是凄凉,阴森一些,胡同走道很相似,你们是生人,加上心理上有些不适应,别的也没什么,其实习惯就没事了。”
水多鱼蹲下来接着说道:“这里住了四五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都是爹不疼娘不爱,路人见了就想踹上两脚的主儿,街上的人说我们手脚不干净。
那我们也是没办法才会做些偷鸡摸狗的事,因为哥儿几个有些时候手头紧。
他们有事需要我们帮忙干杂活的话,还是会对我们客气点的。”
我对水多鱼说:“你在街上摆个摊位卖些小耍具,忽悠忽悠小孩儿,日子不是照样凑合着过嘛!”
他无奈道:“兄弟,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大字不识一个,算盘也打不精,做买卖说不定还得往里倒贴钱,这要是一天啥都没卖那我不得饿上两顿。
俗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肚子里没啥油水,能填饱五脏庙比啥都强。
我从小吊儿郎当惯了,别的手艺没有,这帮人打杂跑腿的功夫倒是一个能顶十几个用,大钱没有,小钱一天两顿对付着足够,在主家干活,赶上饭点还能在人家家里好赖吃上一顿,日子无拘无束过得也算自在。
过两年这里就要拆了重建,估计到时候就要在桥下风餐露宿了。”
阿坤嘿嘿道:“不碍事,现在政府政策好,说不定还能给你们安置几间救济房。”
水多余挥挥手说道:“那都是以后的事了,咱也操不起这闲心,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命我也认了,不认命我也没啥通天过人的本事。”
我见他说的唾沫星子乱飞,就急忙打住他的话问:“郝老六住哪?”
“那家伙天天啥都不干,饿了就到我那里捞点东西吃,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的苦,我挣点钱容易吗我。”水多余埋怨道。
我起身伸个懒腰对他说:“我们找他有事,麻烦给带个路。”
水多余嘴里都囔着,看样子不想去郝老六那里,我站起来递给他一支烟。
他没皮没脸地笑道:“只要有一口烟抽,我三天不吃饭也顶得住。”
我们三个走了大约两分钟,水多余站在一扇与胸口平齐的破窗前。
屋子里传出阵阵打鼾声,水多余抽了一大口烟,把头伸向窗户吐了进去,打鼾声猛然停止。
他扭头对我说:“他这人啊,跟我一样只要是睡熟了你泼他身上一盆冷水,他还照样犯迷糊,但是一闻见烟味儿,立马就精神了。”
“水子,你半夜三更不睡觉,也不让老子睡个踏实,我闻这烟味儿还不算差,赶紧滚进来让我解解瘾。”郝老六大声吼道。
屋里亮起了微弱的烛光,门咯吱一声,郝老六从门缝里探出脑袋,定睛看看我和胖子,先是怔了一下,想要关门,我赶紧抵住门脚。
郝老六又满脸堆笑道:“哟!两位找上门儿来了,进来坐。”
屋子里就一张床,还有一张破桌子,连个椅子都没有,自己的衣物折叠的很整齐,摆放在床头铺着麻袋的地面上,收拾的很是干净利落。
这一点我有点诧异,跟我见他第一面的印象,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作风。
郝老六指着床对我和阿坤说:“就坐床上吧!这地儿小。”
我心想这回肯定有戏。
水多余贼笑着我说道:“你看,路我也带到了,是不是先走一步,明天还要早点到城里帮人家戏班子搭戏棚,要不然后天就要饿肚皮了。”
他搓了搓手,看向阿坤。
阿坤掏出一支烟扔给水多余,然后说道:“真没出息,像你这样的吸法,估计阎王早就盯上你了。”
水多余把烟夹在耳朵上,躬着腰双手一拍呵呵一笑说道:“咱这一辈子,别的不图,但是就好上这口了,这根烟先留着,明天要是饿着没饭吃,就先拿它顶着。”
我觉得好笑,对着水多余摆了一下手,让他先走。
水多余嘴里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走到门口就把烟点上了。
我和阿坤坐在床边,死死的盯着郝老六。
郝老六眼珠子一转笑呵呵地说道:“我就料到你俩铁定得找我。”
我疑惑道:“你闹的是哪儿出啊!为什么要假扮我要找得人?”
阿坤气不打一处来,站起身皱着眉头对郝老六说道:“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四五六来,信不信我卸掉你的胳膊。”他一下子抓住郝老六的手臂。
郝老六吓了一跳急忙说道:“这位胖哥消消气,先坐着,听我慢慢跟你们说。”
阿坤撇着嘴坐在床上掏出一根烟,郝老六赶紧捧起煤油灯去掉灯罩,捂着火苗拿到阿坤跟前。
阿坤点着烟,郝老六也要了一根,接着从床单下拿出一本封面破旧的《芥子园画传》,翻看书本,里面夹着一封信件。
他把那封信递给我说道:“你就是汤新年的后人?”
没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我等这一天有半年了,你打开看看,对你或许有帮助。”
我接过信封反复观察了两边,上面除了用钢笔写的一个大大的X字符号外,还有寄信人A,收件人的名字和地址都没有。
这样的信封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到,我打开信封,里面的内容让我很惊讶。
具体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当年那个拿了珠子的人几年前得了血癌,还是晚期。
现在我已经飞黄腾达,有了自己的公司,但我发现这颗珠子神乎其神,诡秘莫测,很难掌控,能给我财富,也能也让我一无所有,这是个非同一般的物件。
为了安抚内心的焦虑不安,我想尽办法,一定要先找到汤新年的后人。
可事过境迁,汤新年所住的地方早已拆迁重建,寻人计划只能搁置。
写信人A是X的领导,珠子先由X保管。
这封信怎么又会在郝老六手里呢?
郝老六打个瞌睡说:那个李伟就是拿走珠子的人,当时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也是被逼的,他拿了珠子不上交,想独吞。
我平时最看不惯他嚣张跋扈的样子,就把这件事偷偷了告诉了老板,老板找人揍了他一顿,把珠子要回来了。
我问郝老六这封信怎么会在他这儿。
郝老六说:“我是受人之托,把任务完成就可以了,这封信只是一份证明,让你们相信有这么回事儿。”
听了郝老六的一番话我激动不已,珠子终于有下落了。
我身体就像是装了弹簧一样,猛然站了起来一把握住郝老六的手,把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向后仰,以为我要削他。
我双手直颤抖,喉咙像是被什么给哽住了,脸憋得通红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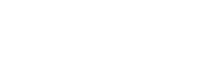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替身一边凉快去吧:番外+完结,秦斐顾时宴云琳琅
替身一边凉快去吧:番外+完结,秦斐顾时宴云琳琅 沈雪枝裴司礼
沈雪枝裴司礼 江风刘雨桐唐灵若
江风刘雨桐唐灵若 兰因絮果谢长乐肖风行
兰因絮果谢长乐肖风行 美女保姆的阴谋
美女保姆的阴谋 三国:董卓逆子,貂蝉说我太坏了
三国:董卓逆子,貂蝉说我太坏了 拾光
拾光 女友怀孕,丈母娘狮子大开口
女友怀孕,丈母娘狮子大开口 狗狗行动队
狗狗行动队 孝子贤孙都跪下,我是你们太奶奶
孝子贤孙都跪下,我是你们太奶奶 绿茶不值得,白月光才是真的香
绿茶不值得,白月光才是真的香 女医生要离婚,霸总下跪求原谅
女医生要离婚,霸总下跪求原谅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辉宝创作的《诡寂》内容很精彩,看的过程真的不想错过一点,看老李阿坤的经历又有些揪心,有些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