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风
我在沾满泥泞的时候遇见谢承泽,以为他能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向通途。
可我错了,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走进那扇大门。或许,他根本感应不到门里的人。
我说:“我得离开了。”
他反问道:“你还会回来吗?”
我是在Chris酒吧遇见他的。
在一个黯淡无星、被霓虹灯侵蚀的夜晚,我正坐在包厢里和一个客户喝酒,强笑着忍耐他的无礼之举。
做这一行,最烦的就是装清高、假洁癖、放不开、摸不下脸。
直到他的手不规矩,我一下子站起来,端着酒杯赔罪道:“王老板,我不搞这个,您点错人了。”
干这一行,客户最大,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谁都得罪不起,所以我们也分了各人负责什么的职务,但总有人仗势欺人,脾性小的忍忍就过了,脾性大点,抗“旨”不遵,结果难说。
王老板就是典型的以为“有钱了不起”,看顺眼了,想玩点不一样的。你一搅他的兴儿,他就得和你翻脸。
“都来你们这儿了,装什么清高呢?你识点相,我可点了不少酒,待会儿砸了你赔?你赔得起吗?”
我扯出一抹笑容,“不好意思,但我今天实在不行,我去给您再找个人。”
说着,我就往门口走去,他今儿心情也不好,在我拉开门之前,酒瓶子已经飞过来了。
我吓得一躲,酒瓶迸碎的玻璃渣咬住了我的腿,鲜血汩汩冒出,王老板吼道:“今天还治不了你了!”
动静有点大,招来了负责人,她一看这狼藉,先甩了我一耳光,脑中传来嗡鸣,嘴里溢出铁锈味,负责人嘴唇一开一合,我听不见也看不见。
王老板对我指指点点,负责人对旁边路过好奇的客人点头哈腰,她一把拉住我的手,骂道:“你个贱蹄子,王老板多大的客户,找你聊聊天你还发脾气,真当自己是公主了?”
“今天你不去也得去。不然拿钱把你自己赎走!”
我没有钱,钱都给了我父母,给我那个患白血病的弟弟续命。
反正,这么多年,我俩之中总得死一个。
守着这副破烂身子,也没什么用。
我认命。
我重新堆起笑容,道:“王老板……”
“你要多少钱?”一个男声在我耳边响起。
“他?”李栖璟玩味地笑着,“让你念念不忘的人?”
我点头又摇头,“不算,曾经我一度觉得我会在他身边待一辈子,现在更多的是感谢吧。”
“感谢吗?”李栖璟想了想,“你还在跟他联系吗?”
“平时节假日会发几句问候,也没说过什么。”我瞅见了他善意的笑,“这已经不算采访内容了吧?”
李栖璟“嗯”了一声,挑眉道:“私人问题。”
“待会儿去吃个饭?顺便再给我讲讲你以前的事?”
我和李栖璟相识是在出版社,他作为记者采访一位很有名的作家,约在出版社见面,我去出版社签出版合约,跟他碰上。
交换了联系方式,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天来。
他是个很有分寸的人,虽然看起来很时尚追潮流,每天骑着摩托飞驰在大街小巷,但他从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也不会打听私事。
我们现在处于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阶段,我能感觉到他喜欢我,只是我很少回应。
再浓烈的情感也会因为没有回应而淡薄,他察觉到,所以放慢脚步。
我说,没什么可以讲的了,接下来的故事千篇一律,你肯定已经听厌了。
他说,怎么会?关于你,我一直很想听。
于是,我们吃完饭去到我家,关了灯坐在地毯上看一部很老很老的片子。
讲刀光剑影中的爱情。
我说,这实在是个无聊的故事。
他说,但我想听。
就这样,谢承泽把我送回了我家,在一个弯弯绕绕又破又旧的筒子楼里,他对我说:“等你以后找到工作再考虑还钱的问题吧,我不急。”
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在酒吧帮忙卖酒,我还会干什么呢?
我呆愣愣地站着,也不回话,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但我急。”我不习惯自己是亏欠方。
谢承泽似乎也思考了一下,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来工作的?”
我说:“高中。”又怕他误会,我补上一句:
“最开始当餐厅服务员,后来餐厅不开了,才到这里来的。”
他说:“那你跟我学写文章吧?”
他是一个好作家,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的眼睛很亮,在漫无边际的黑夜里,洒满了星光。
我说:“好。”
他弯弯眼睛,“这里离我家挺远的,如果你不介意,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对门没人,如果你愿意搬过来,权当帮我守一下房子了。”
“那我要给你钱。”他没推辞。
我收拾齐整东西,把房子钥匙还给房东,房东人好,把剩下两个月的费用退给了我,没收违约金。
我在楼下超市找了份工作,他有空时会教我如何构思、如何描写,故事讲究起承转合,我却写得很平淡。
这是一个坎,他说很多人都经历过,要靠悟,多看书多写。
我开始听书,什么书都看,自然科学、法律、文学等等,后来有时候会帮他看看合同。
每天晚上写点练笔,第二天给他看。
“你明晚有空吗?”他微微偏过头,用那双漂亮的眼睛注视我。
我说:“当然。”
他去赴一个聚会,他的家世不错。
上次去会所,是为了接他一个喝醉的朋友。
还没走进装潢富丽的大门,他的朋友便飞奔而来揽过他。
“哎,这不是上次那……”付言笑着给我打招呼,他给他一肘子,让他别那么大声。
我也对他笑笑:“你好。”
“变化挺大,我让你带女伴,你不要杨小姐,你找这么个小姑娘?”付言向来直率,但没有恶意。
我们进到大厅,绚烂的光影几乎让我目眩,谢承泽给我递了块蛋糕,歉意道:“抱歉,我过去一下。”
他走了没多久,我隐在角落吃点心,一个人挡在我面前。
“哟,这不是Jeanie吗?”我以前的客户,姓康,我只记得他是搞影视的。
他讽刺地打量我,嘲道:“不在酒吧,抱上谁的大腿能带你来这里?”
我一时难堪,微张着嘴说不出话。
电影里,男女主畅游天地间,无猜无疑。
我看向李栖璟,惨白的电影光打在我们俩的侧脸。
“你知道那种,光天化日之下,被人扒掉伪装、处脏污的身体的感觉吗?”
“我不想闹得人尽皆知,顺着他的话说几句也就完了,但是他威胁我。”
李栖璟了然,“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康老板靠近我,摸上我的手腕,猥琐地笑:“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我现在就走。”
皮肤的触感让我恶心又恐惧,我挣脱开他的手,“不可能。”
“康老板。”谢承泽回来了,这样小的事情,竟然让我泪盈于睫。
他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背后,客气道:“上次的事,还没谈好,不如我们再谈谈?”
康老板看这架势,他捞不到什么好处,瞪我一眼,装腔作势地对谢承泽道:“谢少,猫都不吃来路不明的死老鼠,谢先生和谢夫人还不知道吧?”
谢承泽回的什么我没听见,他安抚性地拍拍我,便和康老板去阳台了。
我们俩默契地把这件事情揭过,谁都没提,后来我再也没去过这种聚会。
我开始写诗,谢承泽说我的语言适合写诗。
也许吧?但我觉得是我写不出故事的缘故,我的情节是一条平静的山间小溪,掀不起波澜,就像我这个人。我的语言不算流畅,比不上他们很多有天赋又有学识的人。
于是,我开始写诗,才开始写两三行后面慢慢能写到十行十五行。
李栖璟评价道:“他还挺有眼光的。”
我弟弟死了,在我开始写诗不久后。很难说是伤心多一点还是如释重负多一点,我在那个明媚爽朗的秋日里失去了一个亲人。
我告诉谢承泽,我得回去几天。
他面带歉意道:“抱歉不能送你回去,他现在生活在没有病痛的世界,别难过。”
我勉强笑了笑:“好,只是感觉世事无常。”
他站起身,轻轻抱住我。
我赶回家,父母和帮忙哭丧的都趴在棺材旁,哭得很狼狈。
父亲看见我,爬起来拉过我的手,“宁宁,你弟弟,你弟弟……”
我按住他的手,叹了口气:“爸,该送去火化了。”
我看着血红色的“蒋木宸正在火化”的字样,觉得外面阳光好刺眼。
我抱着骨灰盒扶着父母一步一步走回家。
骨灰盒很重,可人死就在轻飘飘的一瞬间。
我坐车回城市,手机邮箱传来杂志编辑通过我的第一篇诗歌的消息。
窗外的稻田枯黄一片,在艳阳的照耀下更显灰白,我和编辑签好合约,他发给我第一笔稿费,我下意识地转给父亲,输入密码时才意识到,不用了。
父亲让我照顾好自己,不用再转钱了。
我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电影里,男女主同床异梦,各怀心思。
“我以为你会留在家乡,”李栖璟给我搭好毛毯,“你们是怎么分开的?”
我踹了他一脚,不重,“你听不听?老打茬。”
我不留在家是因为我们那一带农村风言风语多,我之前做的工作上不得台面,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留在那里对我父母和我都不好。
至于怎么分开的,只能说世事无常,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走不到一个世界去。
回家后,我想着要给谢承泽说一声,便去敲隔壁的门。
我们俩很少手机聊天,要找对方从来都是直接敲门。
这天,我遇到了他们口中的杨小姐。
是个很美很知性的女孩,他们说杨小姐是大学老师,身世样貌学识都跟谢承泽很配,双方父母也看好两人,唯一问题就在谢承泽身上。
谢承泽婉言推辞一切撮合,他对她没有感觉。
但是,她给我开门的那一刻,真真的天壤之别,丑小鸭遇见白天鹅时的不安和恐慌让我的头几乎要低进尘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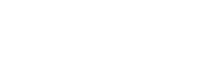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重返1977黄金年代
重返1977黄金年代 月落星沉花未央
月落星沉花未央 青青陌上桑
青青陌上桑 何以解忧
何以解忧 绝世狂医
绝世狂医 烟花冷透两相忘
烟花冷透两相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很多人都说《地尽头》挺好看的,闲来无事我也搜索看一下,结果入了浮梦的坑,果然群众是不会骗人的。内容上就比较吸引人,情节设定上也有不少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