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吗?不懂!他口口声声半年相思难熬,转眼。韵儿抿唇一笑,心底亦是苦笑,这等轻浮情话鬼都骗不过,却独独骗了自己:“给陛下和娘娘道喜了,方才未曾留意,还请海涵。”
明黄背脊僵了僵,轩辕远毅觉到背脊阵阵凉意,字字含笑,那笑里隐藏的疏离唯自己读得懂,比重逢那日更拒人千里。
强贤妃如坐针毡,头先并无不妥,倒险些被皇后吓得滑倒。她瞥一眼暗露喜色的皇后,又瞥一眼面色阴沉的夫君,强挤一丝笑意:“公主言重了,都是。一家人。只怪我身子羸弱,总惹陛下和姐妹们操心,都是我的不是,往后怕是。也免不得叨扰妹妹。”
“好生回去歇着。”轩辕远毅关切地说了这么一句,已有几分不耐地拂手屏退众妃。
李双杵在一侧,好不幸灾乐祸,当下刚要开口,被苟曼青使眼色止了下去。轩辕芸识趣地先行进了内殿。
空荡荡的殿,只剩默然不语的二人。
“韵儿。”刻意压低的声线悬浮在焦躁的浮尘之上,轩辕远毅自觉难耐,男儿大丈夫纳妾生子哪里用得着低声下气地向个女子解释?贤妃几次险些流产,头先这一声叫唤确实惊到了自己,下意识地跑去搀她,本是人之常情。可,怕是惹她多心了,心乱如麻,更有几分心虚,轩辕远毅此刻方觉眼前的女子钳住了自己的命门。
“瞧娘娘的月份,该八九个月了吧?”韵儿倒笑得欢快,眸光熠熠皆染了笑,“听家里的老人说,肚子尖是男娃。娘娘这胎必是一索得男,娘娘诞下麟儿之时,我怕早已回了容国。这儿便提前向陛下道喜了。”
读不懂她的笑,只是她笑得越欢快,心下便越忐忑,轩辕远毅听到“容国”二字,心头更是燃起一把无名火,不由分说地拉起那双柔荑,蹙眉敛眸:“你在想什么,我明白。可,韵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唇角微翘,那丝笑苦而冷,韵儿直勾勾地凝着那双眸眼:“那是怎样?”星眸暗了下来,韵儿不愿多言,可郁集于心的苦水却不吐不快:“八九个月,那时的韵韵,朝不保夕,以泪洗面。她的永玉,呵。我本只是可怜她,比不得那一后一妃,如今看来,她比不得的人,多了去了。”
“我的心你该懂!”水润的眸添了轻雾,轩辕远毅紧抿着唇,愧色爬上眉梢,急色晕红了双颊,“贤儿她身子弱,流产随时会一尸两命。这比不得,不,是没得比,不。是不该比。”语无伦次,更是越描越黑,轩辕远毅只得噤了声。
韵儿漠然摇头,只觉荒凉,每每对他心生一丝希冀,便要以失望乃至绝望收场。此次回轩,更是如此,罢了,韵儿暗吁一气,无心多言。
“母后若不应允,我便去死!”撕心裂肺的一声恸哭。
乍听像是轩辕雨,韵儿蹙眉,眼眶已觉涩涩,朝殿门瞥了一眼:“陛下赶紧进去瞧瞧吧。我是客,不便入内,告退了。”
轩辕远毅顿了顿,眼下千言万语都显苍白,更是无从说起。松开手,轩辕远毅扬指轻轻捋了捋她额角的碎发,比语气更温柔的是那双水润的眸,清波潋滟泛着晓春月色才有的缱绻柔光:“别胡思乱想,在偏殿歇会儿。一起用膳。再聊。”
倚着冰冷的石栏,韵儿仰头望去,天水洗般湛蓝,涤得清澄剔透,亮澄澄得灼眼。韵儿抬手捂住眼,灼痛穿透瞳孔直刺心底,窒闷得透不过气。
“公主。”小草踮起脚尖,伸手便要抽开韵儿的手。
呼哧呼哧不似厚重的呼吸,倒似乏力的心跳,韵儿顺从地抽开手,冲着小草却是美滋滋一笑,笑得眼角弯作了月牙儿:“我是不是蠢得可笑?”
小草悻悻地摇头。
韵儿又是噗嗤一笑,从腰封掏出龙门璧掂在掌心,笑岔了气:“一块破石头,我竟差点被骗了。”
“公主——”小草撅嘴嘟囔,“您要是心里不痛快,便说出来。”
“哪里不痛快?”韵儿拢着龙门璧紧了紧,小心翼翼地纳入腰封,径自低语,径自踱步,“我要的,都到手了。”
拖着步子,一步步靠近那点暗色,韵儿的心一寸寸被揪紧,真是他!他虔诚得似一尊石佛,笔直地跪着,眼眸澄净得不着一丝凡尘。即便自己近在咫尺,那两汪净水里竟未现自己的身影。
对望,他的眼里,竟瞧不见自己。嗓子眼浮起一丝淡淡酸涩,韵儿感到不安:“眀曦,你。在这儿做什么?”
那双桃花眼,冷清得不曾相识,眀曦冷漠地抬眸,双手推了推身前折得棱角分明的僧袍,躺在经书上的菩提珠隐隐滚了滚:“我以这身僧袍,这本经书,这串菩提,向雨公主提亲。”
已然猜到几分,可当这话从他口中吐出,韵儿还是觉得天地轰然,视线瞬即模糊,天边的云在飘,耳畔的风在飘,眼前的他更在飘,四周的一切都翩翩然,都在舍弃自己飘离而去。
“什么!”小草惊呆了,满脸不可思议,“你不是和尚吗?你不是——”侧目瞥一眼主子,小草把话咽了回去。
“为什么?”三字耗尽全身气力,韵儿忆及沉江那日清晨,声嘶力竭地抱着这尊石佛,乞求他怜悯,乞求他带着自己远走高飞,他当真像一尊佛,舍不下他的阿弥陀佛。
眼眸未现波澜,眀曦冷冷地凝着眼前的女子,唇角浮起一丝浅笑:“但听心声。”
“你说过会帮我挡着。我以为,你和他们不同。”韵儿痴人说梦般,屈膝蹲了下来,指尖触及菩提珠,莫名地颤了颤,眸子染了泪光,啪嗒啪嗒泪水沾湿经书。
眀曦清浅一笑,伸手捧着僧袍往怀翼拢了拢,刻意避开那串断线的晶莹:“我也曾以为,你与他们不同。可,不同的是。阿雨。”
冷栗,自己是中了巫蛊魔咒不成?为何自己信赖的人,到头来都要舍自己而去?就在自己掏心掏肺,信得忘乎所以的时候,他们留给自己的,偏偏只有背影。韵儿禁不住悲戚,泪水决堤,木然地伸手去攀小草。小草急忙搀起韵儿。
一步一步,步步诛心,韵儿踱开几步,终是忍不住回头,孤傲偏执:“眀曦,若是我说,不想你娶雨姐姐。随我回容国,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我们一起。浪迹天涯。你会改变主意吗?”
小草惊到,视线穿梭在一站一跪的二人之间。
韵儿的脸煞白,局促地揪着衣襟,闪烁躲避的眸光,不似满溢希冀,倒似羞赧愧疚。
眀曦则满目惊疑,直直望着眼前的女子,唇角搐了搐,顷刻却是狂声一笑,笑得桃花眼沾了泪,终是淡漠道:“你——”
“我说笑的。”韵儿抢白,笑得尴尬寥落,“祝你们百年好合。”转身便走,韵儿捂着腰封,手隐隐硌着龙门壁,碎着步子急急把寥落和哀伤悉数踩在脚底。
漫无目的地疾走,韵儿不知为何悲,又因何逃,穿过一道道宫门,直到走得气喘吁吁,俯身扶着宫墙,才发觉竟到了无缘阁。虚无地靠坐破败的廊椅,韵儿盯着铁栅囚室发呆,许久,凄冷苦笑。
当年信誓旦旦地对轩辕溪说,“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过想借同病相怜希求活命,却不料一语成谶,中了魔咒般,屡屡被弃。自己甚至惨过轩辕溪,若是不曾尝到爱恋的甜蜜,或许繁华落尽时便不至万念俱灰,若是不曾有人以命相护,或许曲终人散时便不至患得患失。世上最伤的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一一失去。
如同手捧细沙,越想抓牢幸福,便越失得彻底。曾那般笃定雍山的相拥相恋,到头来,自己不过是百花丛中的一点淡红,比不得牡丹雍容,比不得芙蓉娇媚,一枚可有可无的木槿,得之,锦上添花,舍之,无关痛痒。曾那般感念冷剑下的以命相护,幻念即便天地都舍弃了自己,回眸彼岸还有一尊阿弥陀佛,到头来,自己不过是慈悲怀里的一叶孤舟,他度了自己一时,剩下的一世苍凉还是只能自己孤身潜泅。
掏出龙门璧摊在手心,韵儿痴痴地抚了又抚,良久,才起了身:“走吧,该还的,总得还。”
寿安殿,苟太后歪倚榻上,面如菜色,当真气得不轻。轩辕芸坐在榻前,乖巧地替母亲顺背,双眼却是忧虑地瞅着姐姐。轩辕雨僵跪地上,满脸泪痕,脸色却是从不曾见过的刚毅倔强。轩辕远毅则端坐正座,清淡的眉目,清淡的面容,却带着不怒而威的凛然。
“哀家跟你前世有仇?你竟是要气死哀家不成!赶紧起来!”手指隔空戳着女儿的额头,苟太后卸下了华贵雍容,十足十被忤逆子女气急的老妪,“提亲?天底下见过和尚提亲的?你不惜厚着脸皮求表舅父保媒,他可睬你?伤风败俗,丢尽了我轩辕家的脸!”
“母后,”轩辕远毅压低嗓音,冲着母亲微微摇头,稍敛眸光,对着轩辕雨道,“姐姐,你先起身回府,提亲一事,容孤想想。”
轩辕雨怯弱地抬眸,实在瞧不分明弟弟的心意,一咬牙便铁了心跪定了。
苟太后愈发气急,紧着拳头捶着榻沿,低吼道:“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便是陛下答应,哀家也不答应!”
“容不得母后不答应了。”轩辕雨直了直背脊,微扬下颚,一字一顿道,“我。早已嫁他了。”
“你。你。”苟太后戳着指,气得直哆嗦。这一句倒真真愕住了轩辕远毅兄妹。轩辕芸平日里泼辣成性,当下却羞红了脸:“姐姐,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
叩。叩。幸在方平及时叩响了房门,缓了缓时下的僵局:“陛下,太后娘娘,龙城公主求见,说有要事。”
“宣她进来。”轩辕远毅起身踱近母亲,覆着锦衾掖了掖,“母后,您别急。姐姐只是一时气话,信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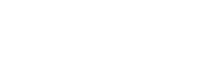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梦中未必丹青见
梦中未必丹青见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何须深情永不负
何须深情永不负 许君千万岁
许君千万岁 宛音如晏
宛音如晏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错遇
错遇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玄灵天尊
玄灵天尊 京城第一绿茶
京城第一绿茶 星河不暗淡
星河不暗淡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很多人都说《流落民间的公主》挺好看的,闲来无事我也搜索看一下,结果入了卿雨轩的坑,果然群众是不会骗人的。内容上就比较吸引人,情节设定上也有不少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