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池神君!南池大人!你只告诉我怎么办?别笑了可以吧!”
我扯了扯他的衣袖,他却不管不顾,只躺在榻上,笑的合不拢嘴,半晌倚了身子,顺了顺气,才道:“阿遥啊阿遥,我同你说过那崖果的核吃不得吃不得,你不听!这下好了,你若是此时回狼山殿,生你养你的阿爹阿娘都指不定认得出来你,哈。”
我只深吸一口气,又拿了他的镜子照了照,左脸那一块绿色延至下巴处,像一片绿色的
“都是你的错!南池啊南池,你那守树的犬未免也太弱了不是?就应该守到谁也进不去,摘不着崖果才好。还有你那设的什么破结界!我上次偷瞄了一眼就学会了,若是难一点,也不至于给我偷吃到啊!不偷吃也就不会这样了!”我反盖了铜镜,看了眼南池,急的要流眼泪。
南池面对我的无理取闹,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却还忍不住走上前来,悠悠地反驳:“你看你这就不讲道理了,是你去偷我的崖果,将我神犬撂倒,把我结界给破了,又是你自己把核吃进肚子变成了这幅模样,还这真的怪不得我,你切莫强词夺理。”
我只叹了口气,摸了摸左脸问:“有办法弄掉吗?”
“阿遥,你剜肉吗?”
“大约什么时候能自己褪去?”
“这个我可没得经验,估计就那么千把年吧!”
“南池!我要砍了你的树!”我站起来,拂了拂纱袖,迈步就要走出去,南池急急将我拦了下来,“阿遥阿遥,别气,我同你开玩笑的!”
“有办法弄掉?”
他偏了偏脸,“方才同你开的玩笑是用不着千把年,最多一百多年就自己褪了。”
……
回狼山殿之前,我一路想了很多办法,最终只变了一条白纱巾,掩了眼睛以下,也好歹看不出来绿成了那副模样。
洛前川从狼山殿院子里的那棵树上跳下来,将我吓了个正着,他伸手就要来扯我的面纱,我只迅速召出不渡扬了扬,他切一声,悻悻地缩回了手:“阿遥,你没事遮脸作甚?”
“我将崖果的核给吞了!”
他大笑,憋都憋不住,我认命似的叹口气,往殿内走去,左右不过是绿个一百多年,罢了!
后来娘亲捧着我的那半张脸端详了半天,说了一句:“不丑的,还怪好看,只是颜色太深,像贴了片大叶子似的,改日寻了丹青娘子用那花汁给你添些花样上去,我的阿遥莫怕,不丑。”
还不丑?还想让丹青娘子添花上去?
对此,我只道了句是亲娘。
早晨起来的时候,小妖婢端了水进来梳洗,见着我突然叫了一声,将手中的盆给打翻,水泼了一地,我迷迷糊糊的坐在床榻上。
见那婢女盯着我的脸怯慌慌的,我才想起来,昨个添了个新鲜的绿印子。
哎,罢了。
坐在铜镜前,拿白纱掩上,左右看着今天的衣裳是鹅黄色的,又找了条鹅黄色的面纱替了那白色的,遮了个正好。
沧山虽是被阿爹解除禁令,但往这边来的人依旧稀少的可怜。
几日前长老们和阿爹商量了一番,封了他为少主,娘亲同我说的时候,我差点闹起来,莫不说燕锦,便是我这样没心没肺的也懂什么意思,龙族不过剩他一人,表面风光称为少主,可本就没什么含义,只是多了一层讽刺罢了。
这儿算是潜派了几个男女小妖过来照料燕锦,修缮座小宅子,坡上杂草被拔走,栽了些红色的招月花,也挪了几颗好看的树过来,勉强看着没有从前那般荒凉了。
院子里身着紫裳的小妖婢在浇花,我定了定神,走宅子里走去。
“你是哪里来的女妖?闯我燕锦少主住处是做什么?”那仙婢拿着扫帚,斜着身子问我。
我只觉好笑,姑奶奶我周身仙气虽然不怎浓郁吧,但好歹是个半仙啊!遂有些气恼的意味反问她:“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是妖了?”
她想了想说:“你掩着面,应该是刚化形不久,脸上还有皮没褪干净的吧?”
记得阿娘从前说,面对这样没眼力的小妖怪不用搭理,可我心情也的确不算的好,手一挥,减去她两分修为,有些泄愤的感觉:“我化形是七八百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刚修到了半仙,我阿娘说昂,身为狼姬,可以不用跟你们这些妖精计较,但是你说的话我极不爱听,所以减你修为,你服不服?”
刚才我刚进门的时候她说啥了?
说我是哪里来的女妖,说我为啥进她燕锦少主的院子。
我是不是女妖另当别论,燕锦几时成了她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妖精的了?
我没回头,走了五六步,只听得后面水壶落地,还有一句:“小妖不知是遥姬殿下,多有冒犯,还望殿下恕罪!”
听她声有哽咽,痛苦的开始蜷缩。
我只记得娘亲平日里教我,阿遥啊,你平日里得端了架子出来,就算没有本事罩身,整个狼山殿都是你骄傲的资本,同枝雅那丫头学学,将自己放的高些。
我只觉得这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便是娘亲为我好的那份心,不对的是,她那引以为傲的,可以做我靠山的狼山殿,本是普通的狼山,从前流荒之主是燕锦一族,该骄傲的人如今却成了这般,不该骄傲的人,却要端起架子,学着骄傲。
虽然是龙族犯了大错才被顶替,但在我心里头,总觉得燕锦比我优秀太多,如若他是未来的流荒之主,应该会比我做的好。
穿过宅子,小径通幽去到那个山中湖泊。
远远瞧见燕锦背对着我,脱了上衣,浮在湖心处,背部有一条一条很长的伤痕,还渗着血,看的我一阵鼻酸,悄悄地飞身在他背后,轻轻的触摸那伤痕。
“阿遥,你来了?”
“这上回翻覆之乱伤的吗?还没好吗?”
他侧了脸望我,穿了衣袍,忽地转了身,拉我到岸边,瞧着我的脸,忽略我问他的,反倒问我一句:“你这脸是怎么了?”
我揪紧了他的衣裳,重重地叹一口气,“燕锦啊,我日后一百多年都要这副模样见人了,那崖果的核吃不得。”
他只取了那鹅黄色的面纱,提了两端边角,小心的替我别在了发髻两边,然隔着面纱摸了摸我有绿色印记的左脸,说的柔和:“那又怎样,也不过一百多年,没谁敢笑你。”
这会儿子出去,倒没见着刚才那个小妖婢。
一同走出这院子,我拉了他转身,“燕锦,你以后都住这里了是不是?”
“有湖泊,我住的习惯。”
我仰头看了眼废弃老久的门匾,:“给这院子起了名吧,总归这也不是禁山了。”
燕锦摸了我的发,又看看这院子,轻飘飘地说道:“禁山也挺好的,也不用改了吧。”
“这怎么可以!”我抗议,同他争辩:“都说不是禁山了,往后永远也不是禁山了!”
“那你想改成什么?”
“要我说,就改成燕锦楼吧?好不好?”
他伸手抚了我的脑袋,笑的颇无可奈何,“阿遥,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这里头住了我这么个人?”
我挑眉,踮着脚尖,伸手捂了他的嘴,瞧着他的燕锦,仔仔细细地说给他听,“那叫燕摇斋罢!燕锦的燕,摇晃的摇,赶明儿往那树上扎个摇来摇去的秋千,这般最好,又有你的姓,也很应景!你说是或不是?”
燕锦眨眼,我便算他默认了,一挥手,门匾变的大气又崭新,烫金大字写着潦草的“燕摇斋”。
也亏得燕锦没有对着三个字再发文,否则我算是遮着面纱,那红色的脸大抵也会给他瞧见了。
他又指了这院子另一坡地方同我说:“你看你喜爱些什么花,种了满院,看着也欢心。”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花儿,但我阿娘说,招月是种好花,懂得逐月揽光,白的素雅,红的艳丽,说花期也很久,代表长盛不衰的尊华。”
他淡淡地说:“你很听你阿娘的话。”
“我阿娘总想让我做一个至高无上,世间最尊贵的女人,她总约束我,却也总宽慰我,她说我是雪狼一脉的天选,要我永远地璀璨下去。”末了,我又补充一句:“阿娘待我很好,生我的时候,废了她半身修为。“
“你阿娘的确对你很好,阿遥,其实我想说,如果你并不喜欢临于绝顶,也不必勉强自己去面对那些,有的时候,背负的越多,过得也便越辛苦。”燕锦还是第一次同我说这样的话,让我有些错愕,以至于嘴一张,也问了我这些日子以来,最想问的问题,我问他,恨不恨我阿爹当了流荒之主,恨不恨他如今沦落到这样的境地。
他摇摇头说:“阿遥,是非因果,不由分说。”
后来有一回,南池来这处,瞥见那烫金大字对我打趣:“燕摇斋?阿遥,莫不是这“遥”字写错了?需要我给你改一改吗?”
我呛回去:“劳神君挂心,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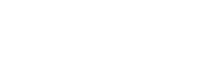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梦中未必丹青见
梦中未必丹青见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何须深情永不负
何须深情永不负 许君千万岁
许君千万岁 宛音如晏
宛音如晏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错遇
错遇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玄灵天尊
玄灵天尊 京城第一绿茶
京城第一绿茶 星河不暗淡
星河不暗淡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亡狼调》所表达的内容是比较新奇的,怪不得有这么多的读者会喜欢,而且芜深的文笔又非常不错,刻画的燕锦牧遥形象完美,非常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