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受毒打和欺凌,那个过程,我毕生难忘。
也不知道是谁,或许是出于对我极力反抗的愤怒,拿了茶几上的烟灰缸砸在了我的脑袋上,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像是开了花一样,一股温热的东西顺着耳朵流了下去,我的双手依然死死地护住我没了遮挡物的胸口。
我当时就在想,死了吧,死了就结束了,没有丈夫的不忠,没有闺蜜的背叛,没有婆婆的辱骂,也不会再有这笔飞来横祸般的巨额债务,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就解脱了。
但他们对我拳打脚踢的疼痛,却清晰的在我身上的每一个角落里传送着,还有几个男人不怀好意的猥亵,夹着我厉声的哭嚎和女人们禽兽般放肆的笑声,那扇打开的大门已经关闭了,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隔着那扇门我都能听到他们威胁邻居不准报警的声音。
在这间充满了讽刺和凉薄的房间里,上演着炼狱至苦的折磨,当那些人的手,不安于扒光我的上衣,对准我的下半身动手时,那个跟着一起哭泣的小女孩,突然间冲了过来,用她稚嫩的小手推着那些企图对我不轨的男人,女人们看着笑话,小女孩的弟弟见状,也加入了这一片的混乱中。
我是真的想死,可我死不了,不仅仅是死不了,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扒掉了下半身的西装长裤。
门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人一脚踹开的,两个彪形大汉都没能挡住那个男人伟岸的身躯,我头晕目眩并未看清他的脸,只记得他脱了身上的风衣,一把将不堪入目的我紧紧裹住,被他抱起后,我看到邻居家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全都拿着家里的扫帚菜刀等一应物件挡在门口,踏出房间没多久,一群警察从电梯里出来,而我终于放弃了最后一丝挣扎的力气,晕在了如天使一般降临的这个男人的怀里。
再醒来时,我听到好朋友杨絮在门口问警察,轻伤二级怎么判刑?能将那些人绳之以法吗?
警察自然是要先了解情况的,但是作为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我的前夫周樊竟然早在一周之前,就带着婆婆和小三出国了。
我的伤势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杨絮给我请了律师,咬着牙说,告,一定要告到底,要将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都送进监狱里去。
但律师告诉我,事已至此,最理智的解决办法是赔偿。
因为对我而言,这份苦难已经造成了,与其结仇,不如想办法度过眼前的难关。
也就是说,在律师眼里,那笔接近三百万的债务,我是挣脱不掉的。
果不其然,三天后,我身上的淤青仍旧历历在目,还没出院的我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这几日我都精神恍惚,也不做噩梦,就是梦到自己回到了五年前,回到了周樊请我吃饭表明心迹的地方,梦到我当时没有接受那束玫瑰花,而是端起了桌上的红酒杯,毫不犹豫的泼在了周樊的脸上。
如果能重来,我一定不会和周樊谈恋爱,更不会步入婚姻这座无处申辩的监牢里。
现在我捏着手中的传票,一场关于正义和尊严的战役,都在我的一念之间。
这一晚上,我想了很多,想过逃避所有一了百了的去死,也想过如何才能拼尽全力好好活着,但天又亮了,律师和杨絮的话,分别在我的脑袋里打架,律师是理性的,如果能得到一笔赔偿款,就能减轻我的债务,但杨絮坚决认为,我现在的退让,只会让以后的处境变得更艰难。
如果一个人连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本能都没了,不就等于赋予了别人伤害你的权利吗?
律师让我想想父母,如果我愿意和解,他会帮我最大利益的去争取赔偿款。
在医院病房里,杨絮怒不可遏的拿着削苹果的水果刀把这个所谓的毫无败绩的律师给赶了出去,我知道,她背对着我的时候偷偷的抹了把眼泪,一转身又笑着安慰我说,一定会给我找一个最好的律师,还我一个公道的。
作为朋友,她为我做的已经够多够好了。
就连律师都不愿意为我辩护,可见我的处境有多艰难。
看着我一脸苦笑的样子,杨絮红着眼问,要不要把你离婚的事情和这件事情告诉叔叔阿姨?
我拼命的摇头,结婚的时候妈妈就说过,周樊没有担当,但我以为,普通人的日子都是平平淡淡过的,只要我们生活过的去,不求飞黄腾达,只求小富即安。
谁知道周樊就是我命里的劫,我不想让爸妈知道我的处境,我从小就是他们手中的掌上明珠,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们见了,该有多伤心。
但瞒是瞒不住的,找上门来的那位老人,为了讨回八万块钱,不知从何处打探到我爸妈在老家的住址,直接找上门去了。
我的生活彻底坠入了地狱,勤勤恳恳一辈子教书育人的妈妈,在得之我的处境看到我一身伤痕后,心脏病复发被送进了抢救室,而我那如山一般的父亲,也一夜之间白了一半的头发。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真的不会相信,真的会有人一夜白头,杨絮说,这种锥心的痛,只有做了父母后才会懂。
但我不仅仅是无能为力,杨絮托人找了很多关系,一些有名气的律师,都不肯接我这个在他们眼里必败无疑的案子。
也就在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在那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敲响了我病房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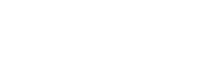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公子,何不成尸仙?
公子,何不成尸仙? 蜂蜜色的尖叫短篇小说合集
蜂蜜色的尖叫短篇小说合集 重生嫡女医毒双绝
重生嫡女医毒双绝 新生别爱
新生别爱 情不知所起,念你成疾
情不知所起,念你成疾 假千金?我是真千金
假千金?我是真千金 帅大叔
帅大叔 她选白月光那天,我收购了她家公司
她选白月光那天,我收购了她家公司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口红矛盾
口红矛盾 重生六零:兵王带全家致富
重生六零:兵王带全家致富 遗忘
遗忘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看过《婚牢》之后久久不能忘记其中很多场景,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如此好看的作品了。真的很希望可以将发生在曾晚周樊身上的故事拍成影视剧,这样就会有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