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来人间时亦是大雪冰封,逢人界危难,行号巷哭。
我实在奇怪,肝肠寸断究竟是什么感觉。
于是扬腿,踢了扇灵一脚,「打我。」
「我要哭。」
扇灵吃瘪,不耐烦地喊到,「你可是为世人散播快乐的喜神娘娘啊!」
他嘟囔,「喜神,怎么会哭呢。」
扇灵,你骗人。
喜神明明也会哭。
我抵住杜濯起伏胸膛,不可置信地问,「你方才说什么?」
他低眸浅声,「晚晚怕疼。」
我在入神籍千年,虽香火不旺,却也不至于沦落到要替别人生孩子。
神明,自有神明的尊严。
我冷笑,「凭什么?」
况且他知,我也怕疼。
他不耐烦地起身,徒留满床狼藉,「扫兴!」
我追出去,看到方才还冷着脸的杜濯正在不远处同徐晚晚笑谈。
举止亲密无间,像极了恩爱夫妻。
杜濯走后,徐晚晚扭着腰向我走来,她假意扶了扶头簪,「王爷向来火急火燎的,姐姐别在意。」
她发间的步摇在余晖下明灿灿的,与我头上的半分不差。
这本是我与杜濯成婚时他亲手为我打造的,他说,「阿悦,唯有你配得这样举世无双的东西。」
可如今,他轻易将它送给了徐晚晚。
后半夜,我张开手掌,天帝的封印若隐若现地蔓延至指尖。
我抿唇,背上细软欲离开林王府。
一道剑气犀利地划过,杜濯的目光落在我的包袱上,「你想走?」
徐晚晚缩在他身后,手中提着花灯。
我忽得记起,我与他的初识是在灯会上一同为摊主出头,他衣袂翩然,剑未出鞘便将一众地痞无赖打得倒地不起。
末了还不忘回头挑眉,满脸少年的张扬之气,「这等小事不必姑娘出手。」
他为人,我为神,但我们一样渴望人间正道,便结伴快意江湖。
他握长剑,扶贫救世。
我执小扇,散播喜乐。
那半年,我们生死与共,满腔少年侠义。
「我讨厌陷入你与徐晚晚的情爱之中,」我将嵌入木门的剑取下来递给他,「杜濯,放我走吧。」
他愣了半瞬,仰首挥斩接过的剑,「可以,留下此玉你便自由了。」
腰间一轻,无暇沉白的和田玉砸在地上,蜿蜒出几条裂纹。
我心下大惊,连忙去捡。徐晚晚趁机踩住我的手,言词傲慢,「神明如何,不照样被我踩在脚下。」
她脚尖狠狠碾了一下,十指立刻传来钻心的疼痛,掌下的玉彻底碎成了两半。
「江时悦,不许动她!」杜濯口中惩奸除恶的长剑正悬在我的眉心。
我扳徐晚晚的手滞在半空。
原来,我竟是拆散他们的奸恶之人。
过往数不清的年月里,我秉承神祇之责,广爱世人,从未像此刻这般怨恨谁。
偏杜濯,又是我最深爱之人。
一股酸涩哽在喉中,我抽出步摇抵在他脖颈,浑身颤抖,「杜濯,你明知道这玉对我意义非凡……」
他攥住我的手腕,将我甩到墙上,凸出的砖瓦咯得我脊背生疼,可他的眉眼却徐徐转向身侧之人,「不过一个扇灵。」
「为了晚晚,就算要牺牲天下万民又有何不可?」
他揽着徐晚晚从我身前走过。
寒风刺骨,遗落的花灯在雪地里转了两圈,骤时燃起火,不过眨眼间便只余焦黑的竹架。
杜濯向我表明心意时,送的便是花灯。
枯树断崖,我们并肩席地而坐,花灯中的盈盈烛光晃荡摇曳。
我唰得合上小扇,「如此多貌美女子倾心于你,你竟没有一个中意的?」
「我要扬名江湖,除不平事!」杜濯清咳一声,话音却更低,「若真要成家,也得是与你。」
我惊道,「我?」
他正身,微弱的火光恰好打在他脸上,「江时悦,我喜欢你。」
「除却大义,我只想与你共赴山海。」
我被他吓了一跳,「可我是神明啊。」
他诚挚发问,「神明,便不能被爱么?」
我垂首,地上的灵玉早已恢复如初。
它蕴含神力,三界六道仅此一枚,可扇灵的最后一丝灵识却归于虚无。
脸上痒痒的,我抬手抹了一脸的泪。
仰头,见白雪纷飞。
我初来人间时亦是大雪冰封,逢人界危难,行号巷哭。
我实在奇怪,肝肠寸断究竟是什么感觉。
于是扬腿,踢了扇灵一脚,「打我。」
「我要哭。」
扇灵吃瘪,不耐烦地喊到,「你可是为世人散播快乐的喜神娘娘啊!」
他嘟囔,「喜神,怎么会哭呢。」
扇灵,你骗人。
喜神明明也会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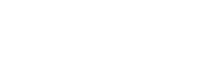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梦中未必丹青见
梦中未必丹青见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渣父子偏爱青梅?她转头离婚独美 何须深情永不负
何须深情永不负 许君千万岁
许君千万岁 宛音如晏
宛音如晏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修仙:从矿奴开始荒野求生 错遇
错遇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被婆婆拆散的婚姻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大反派,从冲撞美艳师尊开始 玄灵天尊
玄灵天尊 京城第一绿茶
京城第一绿茶 星河不暗淡
星河不暗淡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持花梦》中有很多内容的设置非常惊喜,好喜欢安白的文笔和描绘故事的方式,决定以后要追安白的所有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