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彦霖宠了我整整十年。
我以为我们会顺理成章的在一起,结婚,生子,幸福一生。
哪怕长长久久得留在这农村里,我也甘之如饴。
直到宋彦霖带回来一个女人,告诉我:“夕夕,她会是你的大嫂。”
黄子怡笑的娇羞:“妹妹好啊,这是我从城里特意带来的巧克力,送你做见面礼。”
宋彦霖明明应该知道,我吃巧克力会浑身起红疹,甚至呼吸困难。
可他却冷脸对我,“为什么要为难子怡?杨朝夕,你已经不是小丫头了,做事应该有点分寸。”
夜里,我强忍着难受,翻出了原本已经压在箱底的家书,提笔回信:
“爸爸,我想清楚了,来接我回家吧。”
我放下笔,怔怔出神。
夜已深,外面一片黑暗,只有我身在的小房间,还亮着一盏微弱的油灯。
已经是1983年了啊,我来到宋家,已经整整十年了。
我曾经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如今看来,却是我太过天真了。
我自嘲地笑笑,左手无意识地挠着右手臂和大腿上的一片一片红疹。
好难受啊。
身上和心里,都是痒麻又疼痛。
眼前又浮现出了黄子怡委屈咬唇的神情:
“这可是文工团去城里表演得来的奖品,我自己都舍不得尝一口呢。”
是啊,这个年代,巧克力可是难得的稀罕物什,村里的供销社甚至都没有。
可我确实吃不了巧克力啊。
十年多前,妈妈第一次抱着我来敲宋家的门,就是因为我浑身发红疹喘不过气来。
宋彦霖的妈妈是村里的卫生员,和我妈妈盘了半天,才得出结论。
是因为我吃了妈妈珍藏已久的巧克力。
那还是她作为知青下乡,小心藏在包袱里的。
那晚,我浑浑噩噩地在宋家打了一夜的点滴。
而十三岁的宋彦霖,小大人似的跑进跑出,帮我打热水、洗毛巾。
他说,“这个妹妹好看,像个瓷娃娃。她生病了可真让人心疼。”
那时起,我就记住了,我是不能吃巧克力的。
可宋彦霖忘了。
其实此后十年,妈妈扎根在这个村里劳作,再到病逝前将我托孤给宋家,我其实也没机会再见到巧克力。
他一定只是忘了吧,否则怎么会逼着我吃下那块巧克力呢?
我试着去解释,“哥,我真的吃不了,你还记得十多年前……”
可宋彦霖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子怡一片好意,夕夕,你应该给她个面子的。”
他在逼我,认下这个嫂子。
于是我吃了。
只吃了半块,熟悉的呼吸不畅的窒息感便汹涌而来,我冲到门外就干呕起来。
黄子怡很失落,语气甚至染上了一丝哭腔:“夕夕,你是不是不肯接受我?那也不用这样针对我吧?”
我张了张嘴,想辩解,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喉咙哽住,身上也开始仿佛有蚂蚁在爬。
我真的没有要针对黄子怡。
我只是有些想不通,明明之前把我捧在掌心里的宋彦霖,怎么就突然间爱上了别人。
我只是,吃不下这块巧克力啊。
宋彦霖见我也反应这么大,怔愣了一下,却又很快沉了脸色:
“杨朝夕,你太任性了。哪怕有情绪,也不该浪费粮食。你是不是小布尔乔亚的毛病又犯了?”
他很久没有叫我的全名了。
何况这话,说的真的很重。
我虽然十岁就跟着妈妈下乡插队来到这里,身子却一直还是文文弱弱的。
可从前,宋彦霖是很护着我的。
那时他还没当上小队长,却总是在我干不够活攒不够工分时,默默地帮我。
生产队的人常常打趣他,“彦霖对朝夕可真好啊,一看就是个会疼人的。”
他脸都红到了耳朵根,手上的活却不停,只说:
“哥哥帮着妹妹,总是应该的。”
后来再大些,宋彦霖当上了生产小队的队长,也托人送我去了供销社面试。
托妈妈的福,我识字,会算术,成了供销社坐柜台的出纳。
倒也不用再下地干我怎么也擅长不了的农活了。
不是没有人说过闲话的,可都被宋彦霖压下去了。
村里人都知道,年轻力壮的宋队长和谁都一团和气,唯独家里的养女杨朝夕是他的逆鳞,谁也说不得。
可现在,他有了更想护着的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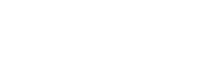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亮出马甲,着急离婚的他瞬间慌了
亮出马甲,着急离婚的他瞬间慌了 姜泠音楚沉渊
姜泠音楚沉渊 乔晚笙裴靳舟
乔晚笙裴靳舟 婆婆非要带女儿亲近大自然
婆婆非要带女儿亲近大自然 亡国后,我被敌军绑上转盘
亡国后,我被敌军绑上转盘 与君别后,恰逢春
与君别后,恰逢春 爱不会随着死亡褪色
爱不会随着死亡褪色 死后穿成恶毒女配
死后穿成恶毒女配 光在爱意消散时
光在爱意消散时 结婚那天妻子将我扔进马厩
结婚那天妻子将我扔进马厩 与君绝
与君绝 前世美貌小仙女一朝重生
前世美貌小仙女一朝重生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这是很多朋友推荐给我的,刚开始看没觉得心动,看到后面一发不可收拾,想不到默问写的《莫问归期》竟然如此的精彩,如此的有意思,决定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