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情桃花:谁杀死了我》 章节介绍
《迷情桃花:谁杀死了我》中每一位人物都很出彩,梁上君子所创作出来的人物个性突出,故事内容冲突不断,很有看点,以下是小说第9章讲述的内容:我坐在冰凉的石凳上,我还在继续灌我的“勇士牌”红酒。看着头顶对面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我的心在颤抖。我即将离......
《迷情桃花:谁杀死了我》 第九章 东子和我 在线试读
我坐在冰凉的石凳上,我还在继续灌我的“勇士牌”红酒。看着头顶对面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我的心在颤抖。我即将离开这个人世,这个令我留恋又厌倦的世界。我那时已经开始有些迷糊,脑海里泛起很多碎片式的记忆。
我多想念承德的山呀,那么多缤纷的秋叶。山总是以排列的阵容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们东子和我。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残留下的痕迹里,那些皇帝们避暑的园林确实精制而奢华。可更加艳丽的是那个深秋里的爱情,是我和东子,这个小我四岁的男人的姐弟恋。
那次,东子的手似是普通的亲近那样自然而然的拢在我的腰间。那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游,而且那会儿我真是他认作的“老姐”。关系单纯。那次,时时刻刻以他的手寻找我的手。是相依为命的那种。
他那么一声声念叨着“老姐”这个吧,“老姐”那个吧的。我就有种说不出的亲切,一股难以消褪的温情就洋溢在我的心间。对这个男人,我有种难以言表的感觉,不是那种青涩初恋的激奋和惶恐,而是似曾相识,是邂逅。第一次看到这个男人,我就有一种亲切,我原本是一个矜持的女人,不会轻易对一个男人产生出这样的情感;但东子不一样,东子是那种你会一生只遇到一次的,人们说什么一个女人的真命天子的。
赛娜汉堡店的那个喝了一点啤酒的中午。他说:“我一直想有一个姐姐(他父母只生个弟弟给他),真想。你就做我的姐姐吧。让我可以依赖你也可以照顾你。”他伸出手来要我的手,从桌子上面,然后很认真的握了我好一会儿。
姐姐,我不知道。他的心理到底要什么。但我却是愿意的。愿意以某种方式与他连接在一起,共同面对许多东西。
我是有姐姐的人。她并不是我的亲姐姐,但却是一个从小带我到大的姐姐。我尊敬和深深爱着她。
我的这个姐姐有个我称作“农场”的地方。其实那地方几近荒漠,那是个集中养殖“小北寒羊”的地方,人烟稀少。
那里到处是荒凉的砂石。那里的黄沙很细很细,可以光着脚踩,风写下的规则的痕上有许多羊的脚印和黑色圆圆的羊粪球,很干爽很纯净,我很乐意踩在上面。
第一次去姐姐的“农场”,是个刚刚显露一点点草色的初春。我和姐姐跟在她的大羊小羊后面往小小沙丘那边的树林里走。羊们肯定是闻到了刚刚冒芽的青草的味道,很激动的样子。小羊的快乐这么明显而实在。我都有一点感动了,记得那时我就好像突然发现自己有了创造某种幸福的能力。
树在沙地里生长的很顽强,很粗壮。凹地里有水。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天空是那样的蓝!蓝得你的心都会害怕跳动着就惊吓了,戈壁是那样的辽阔和安静;尽管我知道这样的安静只是它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显得壮阔,显得雄浑。
很柔美的太阳,淡黄色。没有风。话一出口就撒在空气中。
“只要看看羊们那匆忙而且满足的嗅闻和啃咬,生命的美妙就一目了然了。”姐姐说。我们在树下坐会儿,过一会儿在越过那条火车道去接路易(路易是姐姐的小女儿,从那里放学回来,是周末。)给她一个惊喜(姐姐平时不住这边,只是偶尔来看女儿和羊。这边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所以让女儿上这里的学校)。
早晨,在姐姐家饭前洗手时,姐姐说:星期天我去那边(指她的羊群和有小女儿读书的地方)搂她睡一宿,就回来。丝丝缕缕都只有我不曾体会却可粗略一窥的血脉。我不太懂。只知道我的生命中从未有过。人的生存,这么互相给予着,互相牵挂着,互相惦念着。制造些可以一时的欢喜和可资日后的美丽记忆。这样连带的一些辛苦和艰难不但算不了什么,甚至还是一种目标和乐趣呢。人们的心因此而柔软而忠实而温暖。人生具体而实在。
那条路易将放学回来的公路旁的火车轨道。我和姐姐在上面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又在上面站了很久,踩着发亮的铁轨和黑黑的枕木。
两边都是隐如树林的远远的尽头那种未到尽头的尽头,在意念中延伸。我有点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火车铁轨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比如海子。比如随便一个普通的绝望的人。也比如一个或某影视剧集的导演和摄像师那对于人的视线来说是无限延伸的平静而坚硬的轨道。
我希望我会懂。
在铁轨经过一列不长的旅客稀少的火车后,姐姐回忆起我六岁时的夏天,穿着她亲手为我缝制的有一朵大葵花的蓝色条绒大兜肚的背带裤,她领我去她上学的学校。她的同学和老师都问她:这是哪来的小孩儿?看样子不像咱们这地儿的。
那么小的一个孩子,还没有去过离家100里以外的地方,就显露出一种莫名的异乡人的拘谨和怯弱。
还有后来中学的地理老师(一个北京在当地落了户的知青)的问话:你是从哪搬来的?
再有姐姐一次住院时她的一位病友(某剧团编导)那奇怪的眼神……
就这样,我是养大我家乡的异乡人。是我生活的城市的外地人。我没有可以互相认同,互相融入的家乡。我游离于城乡的任何一种生活之外,人们以喜爱甚至是向往的疏远目光轻掠我。那最好最虚妄的客气的温情给我,我悬浮着。
当我想涕泪横飞地实实在在哭上一场时,却从来不会有迎上来的最相宜的怀抱。
我和姐姐坐在那条铁轨与公路之间的枯草上一直到太阳快落下去。一拨一拨好奇的小学生望着我们并议论着经过。但没有姐姐的小女儿。
我们互相错过了。这也再一次证明了,生活它是不由你来事先安排和设计的。它只由这它自己的意愿随意展开。
张爱玲在她的《小团圆》里写过这么一段话,她写道:
“那痛苦就像火车一样轰隆隆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我知道这种感觉,这种被时间不知不觉催促着走下去的感觉。痛苦没有空隙,那么幸福该如何是好呢?
那个窗口仍然亮着。而且仍然是那一个窗口亮着。
东子是个信命的人,他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在手指上一节一节数着口中嘀嘀咕咕地念叨起来,结果会停在一点上,说这一天如何如何的。我每次都只是笑。
大约九点半,我的头已迷迷糊糊的,药性在发作。我怕会来不及看东子最后一面,就急匆匆往东子的家走去。
站在他家的门口,有断断续续的电视声音和小女孩声音传出来。我靠在他家的鞋柜上,我继续喝酒。我想不好是把《欣儿作文》放在鞋柜上等他自己看见,还是敲门进去给他。我的注意力很涣散,头脑里还有一个念头在闪闪烁烁地出来,他的书房会有床么?他的书房会有床么?
我听见开门的声音。我还是下意识地敲了门,是东子的妻子朱小燕打开的门,她是个看上去很娇小的女人,在我这么个一米七的身材对比下,就显得那么矮小,衣着也是随随便便的主妇装束;我突然发现这个女人,这个拥有着我爱的男人的女人如此平凡普通,普通到让我在那一瞬间有种彻底失败的感觉。还有个小女孩,挺小。只记得她看着我时眼里的好奇困惑。那是双很大很明亮的眼,和她母亲的一样,却能让你看了无法不心存善良!孩子的眼是那样地明亮,就像清澈的流水。恍惚中的我努力去避开这对眼睛,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很荒唐,也很无聊。我干嘛要跑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就呆在自己那个家里悄无声息地死掉?
恍恍惚惚中我看到了东子,他站在那,呆若木鸡。
我绕过朱小燕和东子,径直去了东子的书房。老天保佑,靠窗摆着一张单人床。我坐在床上。把文件袋拿出来。然后,再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近三点钟。
后来,据东子告诉我,我进去他家的全过程是这样:一进门,我便脱鞋,还对他的妻子主动做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已在他家中老老少少的口中响彻了一年,包括他六岁的女儿,都知道有个李红霞的女人存在着。我说了句“我去谭冰房间”,就径自进了他的书房。坐在他的床上。我把酒瓶递给他,要他喝。他出去给我到水,再回来,我已躺在地板上,手里是那个牛皮纸文件袋。他把我扶上床时我一直紧紧的搂着他。直到很快整个人软下来,失去知觉。整个过程,他妻子朱小燕就那么看着。我不知道朱小燕在怎么想。
我是十点多被东子呼叫来救护车,然后直接送往他一个最好的朋友所在的陆军总院的。在救护车上,他的朋友发现我的瞳孔有些放大,但没跟他说。他的人那时除了“怎么办”这几个字已不会说别的了。我被抬进抢救室五六分钟后有一个被扎上肚腹的人来急救。但我在里面,他只有在走廊等。第二天,听说那个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哪儿?”这是我对东子的第一句话。
“你没事了。这是医院。”东子仍握着我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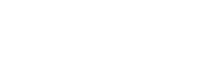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迷情桃花:谁杀死了我
迷情桃花:谁杀死了我
 神豪系统太过分,一万亿目标怎么花
神豪系统太过分,一万亿目标怎么花 白眼狼们集体重生,这回她不管了
白眼狼们集体重生,这回她不管了 恋爱脑驯服计划
恋爱脑驯服计划 重回高考前,打脸成绩作假的追星状元妹妹
重回高考前,打脸成绩作假的追星状元妹妹 穿越:我的心声成了克敌关键
穿越:我的心声成了克敌关键 该回西凉了
该回西凉了 深情装傻
深情装傻 我妈相亲对象儿子是我男神
我妈相亲对象儿子是我男神 双花结
双花结 重回表弟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的那天
重回表弟给我介绍相亲对象的那天 天才在九零:我降维打击爆红军工界
天才在九零:我降维打击爆红军工界 我才不要当女配
我才不要当女配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桃运透视
桃运透视 总裁的新婚罪妻
总裁的新婚罪妻 鉴宝大宗师
鉴宝大宗师 神医赘婿
神医赘婿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龙狱之主
龙狱之主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一念神魔
一念神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