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坠永夜》 章节介绍
《爱坠永夜》实在是精彩的很,吸引了不少的读者,佚名文采了得,很值得仔细推敲,在佚名的描述中徐晚晚赵飞翔形象饱满,在人群中很出彩,第2章讲了:7此时,我并不知道徐晚晚为了找我几乎把沪城翻了个底朝天。雾都曾是顾闫想抵达的地方,他没来我来了。漫步......
《爱坠永夜》 第2章 在线试读
7
此时,我并不知道徐晚晚为了找我几乎把沪城翻了个底朝天。
雾都曾是顾闫想抵达的地方,他没来我来了。
漫步在日渐萧条的街头,我时常恍惚以为我是顾闫。
没人知道我暗暗地苦学绘画,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只是因为那样会更像他。
像他,似乎就会离徐晚晚近一些,再近一些。
阴差阳错,顾闫后来半途而废再也不握画笔了。
反倒是我,被捧上神坛成了笔下会说话的天才。
娶了徐晚晚的这十年里也是我的作品最登峰造极的时光。
如今那几十幅作品都陈列在雾都最大的美术馆里。
我浑浑噩噩地待了近半个月,才在展览即将结束的那天踏了进去。
果然如预期,人少了许多。
我裹着大衣如愿轻松地在每一幅作品前逗留。
梭巡过《燃烧》、《囚鸟》,我停在《绽放》前。
身边有人驻足,同我一样目光落在那张枯萎的少年脸颊上。
“绽放,用生命做燃料,却只是一次徒劳的飞蛾扑火。”
她轻笑,笑意却不达眼底。
侧目看向我的那双眼里,像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
这目光让我心生厌恶,毕竟过去的十年里,徐晚晚总是让我有这种感觉。
我往一旁走,她又不紧不慢地跟上。
“你们很像。”
脚步不由停滞,我的手指不自觉地微蜷。
她的声音幽幽传来,“顾闫说过,你比他更有绘画的天赋。”
“也比他更适合去徐家,他说你天生就有翅膀,不会被困住。”
我已经开始手心微微出汗。
她话锋一转,笑意里满是嘲讽。
“但他没想过,你蠢得会自己折断翅膀,甘心做傀儡。”
骤然地心脏抽疼,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回头怒视着她。
“方虞颜,你害死他还不够……”
话没说完,我愕然地看着不远处脸色阴沉的徐晚晚。
她一步步地靠近,高跟鞋踩在大理石板伤的哒哒声让我心慌。
她不由分说地扯着我和方虞颜拉开差距来。
眼底翻涌的愤怒中却透着几分嘲弄。
“新鲜感?你们顾家兄弟连找女人的眼光都差不多啊。”
另一只手却猛然扇了方虞颜一巴掌。
徐晚晚每个字都咬牙切齿的。
“我是不是说过,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8
方虞颜却无所谓这一巴掌。
“徐总,你早答应增加一笔投资,我何苦来找他呢?”
她看向我的眼里尽是不屑。
“你们欠我的是顾闫的一条命,多少都不够赔的。”
我恍惚地听着,眼看徐晚晚一巴掌又要扬上去。
“等等……”
我见过方虞颜。
在哥哥伴随失事航班尸骨无存时,她出现在顾家过。
我头一次见活死人,好像所有的生气都伴随着哥哥而去。
她跪在地上,拼命地磕头磕得额头都是淋漓的鲜血。
“我只想带走顾闫平时用过的东西,衣服也好,随便什么都好。”
但盛怒之下的父母只是发了疯地捶打她,让人将她架起来丢出去。
徐晚晚已经回过神来,收回手。
似是不耐地摆了摆手,“你走吧,按你的要求去找我的助理。”
随行她而来的人在她一挥手后,就要抓着方虞颜往外走。
我急急地往前两步,“等等,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徐晚晚拦在我面前,纤细一双手攥着我的手腕。
“没什么,跟我回去。”
我奋力地挣脱开来,冲过去抓住方虞颜的衣襟。
“你不就是要钱么?我给你,把你刚才的话说清楚。”
心脏砰砰地跳,前所未有的恐慌感几乎让我的呼吸变得凌乱。
方虞颜已经甩开束缚,好整以暇地越过我看着徐晚晚。
“上个月,在我苦等你那笔投资的时候,我好像想通了很多事。”
“十年,足以证明我的确不适合做商人,换了再多的赛道都是打水漂。”
“所以在听说你们要离婚的消息后,我彻底释然了。”
“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自由的人,唯一可惜的只有我的顾闫。”
她抬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当年订婚礼前夕,徐晚晚很清楚顾闫要逃走。”
“接应他从顾家脱逃的人都是徐晚晚安排的,连机票……”
“也是徐晚晚订的。”
有什么回声在耳边涡旋,久远到重回十年前的那一幕。
隔着门板,我听见了我父母对徐晚晚低声下气的探询。
“要不提前举行婚礼?反正只说徐顾联姻,又没说是哥哥还是弟弟?”
停滞了几秒,徐晚晚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地传来。
“越快越好,我还不想徐家的名声落得和你们家一样地步。”
9
方虞颜笑得肆意。
“你费尽心思嫁给他又能怎么样?用十年的时间让他成了整个沪城的笑话。”
被人这样揭穿窘迫的处境,我只觉无地自容。
可仍无法理解徐晚晚当年为何要帮哥哥逃婚?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放走了他,却还来刁难顾家?”
徐晚晚紧抿着薄唇,许久才出声,“我那时爱的又不是他。”
“是你父母会错了意,想用顾闫当筹码。”
“我一趟趟地去顾家,我和顾闫做任何事都会带你一起,可惜你从来不正眼看我。”
我几乎以为自己耳鸣了,竟然在徐晚晚的声音里听出一丝不甘。
她蜷着的手松开来,落寞地盯着我。
“我成全了顾闫,也如愿嫁给了你。”
“可我知道从一开始你就是身不由己的,顾闫的死,顾家的诸多算计,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不觉苦笑。
逾越在我们之间的又何止是这些?
方虞颜走过来,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个泛黄的信封递给我。
“顾闫留给你的,十年前,如果他顺利抵达,可能这封信早在那时就该送到你手里了。”
信封有焦黄的痕迹,里面是两张过期的票根。
附着的小纸条上是顾闫的字迹。
【阿珩,勇敢一点,像我一样才会幸福。】
徐晚晚眼神暗淡,一把抽了过去。
随即不可置信地抬头看着我。
心底的疏离感再次翻涌而上,我缓缓地抬头看着她。
“顾闫其实什么都知道。”
“知道我那时有多喜欢你。”
“还记得我无疾而终的第一次个人展么?整个画廊里挂满了我笔下的你。”
苦涩的笑在唇边浮动,“怕哥哥看了难过,我还掩人耳目地挂了几幅给他的画像。”
“当作送给你们交往一年的礼物。”
我筹备了整整三个月,惴惴不安地把票根放在了哥哥的抽屉里。
下楼就被欢愉的气氛迎头棒击。
次日,是他们的订婚礼。
10
画笔下的语言是不会骗人的。
顾闫一定早就看过很多次我偷偷用白布盖着的画架。
看得到我在描摹徐晚晚时那些缱绻无处诉说的心绪。
现在一切都揭开,我也终于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过往。
去坐摩天轮的那次,他故意说自己恐高,撺掇着我去和徐晚晚一起。
等我们并肩下来,他笑盈盈地盯着我看。
“别说,你们俩这么瞧着还有点般配。”
我瞬间心如鼓雷,以为隐秘的心事被哥哥看穿了。
徐晚晚却在一旁避开了眼,“顾珩?我俩拜把子还差不多。”
语带轻佻,“闷葫芦一个,来,叫声嫂子,以后我罩着你。”
我飞快地避开他们,心跳的声音却被涌动的哀愁压制。
那次之后,我总会借口作画躲进画室。
避开他们的邀约。
年少时未能水泥封心,好在徐晚晚现在用十年替我封得死死的。
再迎上她的目光,我已没了怦然。
她眼里的欣喜也转瞬即逝,更多的只剩了茫然和无措。
“这么说……当初你……”
都不重要了。
我裹紧了大衣,往外走。
徐晚晚急急地追上来,在美术馆外又一次硬生生地拉住我面对着她。
“为什么不说?我们有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说?”
“非要等到……”
我淡淡地接上了她的话。
“等到一切无可挽回,感情也都消耗殆尽的时候,是么?”
她一时语塞,又徐徐地松了口气,面上久违地释然。
“倒也不至于,我们现在还是夫妻,随时都可以撤回协议。”
我推开她,往后退了一步拉开距离。
“可是,我想要离开你的想法没有改变过。”
她不可置信地盯着我,“就算你刚才什么都知道了,也没有改变?”
“没有。”
她的脸色一瞬间变得难看。
我缓缓地开口,“那一场向你告白的展览没能给你看,我曾经很遗憾。”
“现在这一场展览我以为你不会有兴趣看的,所以才选了这么远的地方。”
“既然你来了,看看吧,每一副都是我告别的决心。”
11
《燃烧》是我婚后一个月时画的。
《囚鸟》是半年后她说不要谈爱时画的。
《新鲜》是折翅的海鸥,一整个系列铺满了十米长墙,每一只鸟都代表一个男孩。
徐晚晚的目光不断地梭巡,那只怕我逃跑而紧抓住的手不由地在用力。
我逐帧地向她介绍,“这是你婚后要我解决的第一个前任,喜欢穿白色卫衣,像这只洁白的海鸥。”
“我都称呼他们是你的前任,哪怕是在我们的婚姻存续期内出现的。”
“可他们每一个都不是我婚姻的破坏者,从头到尾在蚕食掉我的只有你。”
他们都是过客,匆匆如流水。
我曾以为他们至少比我好一点,或多或少地在徐晚晚心间留下过痕迹。
但看着她越来越迷惘的眼神,我突然对他们产生了无尽的怜悯。
“不记得了?”
“这一个,你比较喜欢,在一起快一年多,他穿着新郎服拿着手捧花来挽回你。”
“还有这一个,因为被我父母撞见去质问你,你为了他截断了顾家好几笔银行贷款。”
或许是因为这十年里,被父母明里暗里提过太多次无理要求。
再提起他们时,我心底其实没多大的波澜。
但徐晚晚却不由地手心微微沁汗,许久才说,“有么?我……没什么印象。”
三千多个日夜,数不清的前任。
那一墙壁的孤僻没法飞翔的海鸥,入眼一片白,细看脚下却满是泥泞。
我要往《绽放》走去,她生生拉住了我。
眼里是浓浓的无力感,嘴唇微微颤动。
“好了,不看了,我们回去,我以后都守着你,就我们两个人。”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再说一遍。”
她像是松了口气,一字一顿地又重复了一遍,握住我的那只手逐渐温热。
“可是我不愿意了,徐晚晚。”
她衣兜里的手机不住地震动,每一下都提醒着我。
12
离婚费了些功夫,最终走上了起诉程序。
那是我回到沪城后的事了。
徐晚晚的车停在我家楼下,就像从前一样。
顾家空空荡荡,早不是曾经门庭若市的场景。
我走下去敲开车窗,她睁着满是血丝的眼睛看着我。
“你知道我会赢。”
她顿了片刻,无力地说,“我知道。”
却还挣扎着,“赵飞翔……我断干净了,不会再有别人了。”
我轻轻的问她,“那么多人,都没动心过?”
她不做声。
“我想听一句实话。”
她的嘴唇嗫嚅着,“有过,不多。”
也够了。
我暗笑自己的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小心思。
最后一点火苗也被彻底浇熄。
“你说的对,如果你嫁给他们,最后也会像我。”
她神色慌张,“以后不会了。”
“没有以后了。”
她每天吃住都在车里,大概徐家也受不了她迟来的叛逆。
上门的说客一波接一波,却都不得症结。
每个人都劝我继续回去做哑巴丈夫。
13
我冷然的看着眼前祈求我回去的徐晚晚。
张了张嘴,看着她那复杂的神色,开口。
“徐晚晚,或许我们彼此曾爱过对方……”
“但我们爱对方的时间错过了,再回首只剩了痛苦的记忆。”
“这样还有继续的必要么?”
她不作声,只是头微微地垂着。
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地走出去,关门时那么怯怯的。
几天后,阔别十年,我终于恢复单身。
雾都那边传来消息,我展览上的画都被人一股脑地重金收走。
账户上平白地丰厚起来。
再听到徐晚晚的消息,已是大半个月后了。
从前在她彻夜不归的时候,我时常通宵地开着电视。
嘈杂的声音做背景,好像那座空虚的大屋还残存一点人气。
那时我常做噩梦,醒来就收到噩耗。
或许是超速后的车毁人亡,又或是更适合上社会版的桃色丑闻。
现在,听着电话里徐母的哭叫声,我想梦有时是带着隐喻的。
“顾珩,看在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情分上,看在你和她十年夫妻……”
“来医院看看她吧。”
心跳砰砰不止,一路上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比如,走到病房门外,里面爆发出的悲鸣声,让人喟叹到底是迟了一步。
但病房里寂静无声,徐晚晚包得严实,平静地看着我。
“来了。”
14
她只看了我一眼,就扭头看着窗外。
阳光和煦,洒落在雪白的床单上。
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
“这半个多月里,我像之前一样每天去夜店,就算喝了酒也照样不减车速。”
“我身边的男人没有重复过,可奇怪的很,每一个都好像不如从前了。”
我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时间,距离我去签约画廊还有不到一小时。
算上路程,顶多再过十分钟我就该离开。
那边好像不是很好停车,或许我现在就该……
“阿珩,你在走神么?”
她的声音将我的思绪重新拉了回来,我有一瞬的尴尬。
“你刚刚说什么?”
她定定地看着我,面上没了从前那种高傲,只剩了落寞。
“顾闫跟你很像,但他总是很专注地盯着我,让我很不自在。”
“余光不自觉地就会往你身上瞟,看你躲闪的目光,好像跟我一样心虚。”
她的话不由地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多年前。
那时的三人行,的确总是这样的气氛。
我好像从小就是作为顾闫的衬托存在的,像他不那么规整的影子。
避开了她的眼神,我伸手替她掖了掖被角。
手却不由地僵在原地,塌陷下去的那一块被子让我心底一空。
她却笑了。
“这下没有资本了。”
我猝然地抬头盯着她,心血往上涌。
“徐晚晚!你疯了么?为什么开那么快?”
她放在被子上的手微微颤抖。
勾了勾唇角,却再也不能露出半点轻松的笑意来。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去找你……”
她说,她是想去找我的。
但被赵飞翔堵住,非要徐晚晚给他一个交代。
徐晚晚不愿意,开车径直离开。
结果赵飞翔也开了车在后面穷追不舍。
“我只是想逃离他,没想到会出现意外。”
她的眼圈很红,似乎有些懊恼。
也不愿再回到那惨烈碰撞发生的当下。
我站起身来,想要离开。
徐晚晚的声音从身后犹疑地传来。
“你……还会来看我么?”
我没有回答她。
15
画廊开业的时候,门外送来的花篮排了数十米远。
尤为突出的那几个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她。
而赵飞翔的家人拉横幅、开直播控诉徐家的事情每天都在热搜上挂着。
变着花样地希望从徐家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
我每天都会看到或听到关于她的近况。
电视里、网络上,她仍是那副模样,只是眼神变得空洞了。
她坐在轮椅上,脸色有点白。
只有一次,有人冲过去掀开了她的毯子。
空荡荡的裙子下面,像是连同她的自尊一起被剥开晾晒在地上。
她怔怔地愣了几秒才满脸涨红地伸手去遮掩,却越发显得尴尬。
不知最后到底做了什么样的让步,赵飞翔的家人销声匿迹了。
画廊总是人来人往的,热闹都是那些男孩子带来的。
偶尔结伴,其中一个会攀住我的脖颈向另一个介绍。
“曾经的徐先生,啧啧,我觉得你更像她的秘书。”
我讪笑着,“怎么说?”
“头一回见原配劝别人多要点分手费的,简直是苦口婆心。”
几个人都呵呵地笑。
我心底一片沉静,再见面终于不是红着眼的样子了。
却也有那么一些怅然。
那个叫赵飞翔的男孩,到底还是可惜了。
去拿外卖的咖啡时,有个声音叫我。
轮椅渐渐靠近,我对上徐晚晚的那一双眼。
天气渐热,他的双腿却仍被薄毯覆盖。
或许是注意到我目光落点,她有点慌乱地伸手抚平。
“开业这么久,我还没来看过……”
她像是搜肠刮肚地想要找个借口,又或是想好的理由到了这里却忘了。
我笑了笑。
“徐总专门定了一间美术馆放我从前的作品,哪儿还需要来逛画廊呢?”
我俯下身,替她把毯子抻了抻。
“别再让你的人天天跟着我了。”
余光也瞥得到墙角隐进去的黑衣男子,这状态持续了数个月。
徐晚晚张了张嘴,眼神越发落寞。
年轻女人擦着薄汗从二楼的镂空阳台上探出头来。
她扫了一眼徐晚晚,眉心微蹙又舒展开来。
“阿珩,说完快上来,我饿了。”
我敏感地察觉到徐晚晚的手一瞬间攥紧。
不由地告诉她。
“好了,别再来了。”
随即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
才推门进去,那个年轻的实习生已经掩口憋笑不止。
一屋子的人瓮声瓮气地逗我。
“阿珩,这下前妻要气得好几天睡不着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却也只能无奈摊手。
唯一该庆幸的,那天之后徐晚晚没有再出现过。
16
几年后,徐晚晚在手术中多重感染不治。
遗嘱里有一项,会将永久开放她私人的一间美术馆。
画廊的人去了,回来都神情古怪。
“你应该去看看。”
我在一个淅淅沥沥的雨天踏进了那里。
除了我曾在雾都展出过的那些婚后的画作外,我看到了成长期里我的那些不成熟的画作。
很多甚至是我不满意随手丢弃的。
每一幅底下都有一张说明的小纸片。
是徐晚晚的字迹,许多已年代久远。
【阿珩作于XX年X月XX日,他好像又进步了。】
在整个展览走到最后,我看到了一张徐晚晚的自画像。
潦草而凌乱,如果不是她自己注明那是自画像,我一度以为是墨洒了。
同样的,也附了一张小纸片。
【XX年XX月XX日,永失阿珩,是我罪有应得。】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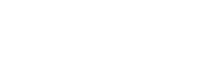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爱坠永夜
爱坠永夜
 男神别跑,等等我
男神别跑,等等我 错青梅
错青梅 夫君的日常眼瞎
夫君的日常眼瞎 汉子婊没有好下场
汉子婊没有好下场 梨花满枝头
梨花满枝头 战神他总想策反我
战神他总想策反我 夫君为庶妹夺我灵芝后,我用七天告别人间
夫君为庶妹夺我灵芝后,我用七天告别人间 给富家少爷的一份信
给富家少爷的一份信 裁掉顶梁柱,负心兄妹悔不当初
裁掉顶梁柱,负心兄妹悔不当初 病态心理师
病态心理师 穿书成娇妻女主
穿书成娇妻女主 紫禁城打工人
紫禁城打工人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桃运透视
桃运透视 总裁的新婚罪妻
总裁的新婚罪妻 鉴宝大宗师
鉴宝大宗师 神医赘婿
神医赘婿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龙狱之主
龙狱之主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一念神魔
一念神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