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馆》 章节介绍
《麻将馆》中的田和平刘黎明作为本文代表性人物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岳峻文笔优美,创作上不跟风,看的很过瘾,下面为大家介绍《麻将馆》第2章内容:第二章“边七万”走在半路上,周芳芳的手机“叮咚”了几声,她知道这是手机微信发过来的声音。她有个习惯,开......
《麻将馆》 第二章 “边七万” 在线试读
第二章“ 边七万”
走在半路上,周芳芳的手机“叮咚”了几声,她知道这是手机微信发过来的声音。她有个习惯,开车就是开车,一般不看微信、不接手机。现在是下午两点多,稳稳地开车到大发麻将馆也就20来分钟。麻将馆一般是下午两点半就开门,何老板舍不得耽误开门时间的。她按了下车上的音乐按键,音箱里就飘出了网络白马市摇滚歌手李笛笛唱的歌曲《手痒你就来麻将馆》:
城乡人们十亿赌
剩下的多是二百五
打牌交际门路广
麻将馆遍地像蘑菇
每人手中十三张牌呐
牛逼得以为自己是老虎
宝贵时光莫空度
手痒你就来麻将馆
哎——看看腰包鼓不鼓
杠上开花门清自摸有财路
城乡人们十亿赌
剩下的都是二百五
聚在一起乐哈哈
多个朋友哎多条路呐
东南西北中发白
条饼万加扔瓠子
宝贵时光莫空度
你打我碰修长城
各自为阵多防护
手痒你就来麻将馆
哎—看看手气顺不顺
缺坎边吊海底捞月龙戏珠
没过了多长时间,周芳芳开车来到了大发麻将馆门前的停车场上。停下车后,她才从包里掏出手机看看上面有啥东西。三朵玫瑰。原来是刚才新加的微信好友“黑老粗”发来的,三个直挺挺、红艳艳的玫瑰图案。看着“黑老粗”这三个字,她多少有点纳闷,文质彬彬的一个郑老板,怎么起个网名“黑老粗”呢?再拨黏了几下,哎呀?支付宝里居然还有一万五千元的进账。嗯?她愣了一下,这突如其来的进账让她颇为吃惊。她坐在车里,想了想,就拨通了田和平的手机,问问这是咋回事。
电话打通后,田和平乐呵呵地寒暄了几句。听到周芳芳问那钱是咋回事时,他一副轻描淡写的口气:“哎——哎,芳芳,你看你这人,郑老板在饭桌上本来就说要送你三朵玫瑰的呀,这,没什么。咋?……你以为他一个大老板,也和咱一样,上下嘴皮子轻轻一碰,给你微信上真的发上三朵玫瑰?哼,尿他还没喝水呢!三朵玫瑰,一朵五千嘛。嘿嘿,对咱来说,数额是不小,可对人家来说,也就一桌饭钱嘛。郑老板,他开的那些煤矿……这么对你说吧,他的那些煤矿,煤炭输送带一天就能从坑口里给他拉上一座或几座楼房来。你想,现在一座楼房卖多少钱?他的钱可海啦。再说,前一段,我给他狗儿的办了几件事,光省就给他省了五六百万。今天中午,在那个破饭店,他请咱一顿就没事啦?一万五千元,小事一桩。你就放放心心地拿着吧,打麻将的零花钱……哎,好啦,就这吧,还有点事儿,一会儿得开个会。”还未等周芳芳再说什么,田和平那边就挂了电话。
周芳芳听见电话挂了,虽然田和平说的轻巧,但她总觉得这事没有那么简单。你给人家帮忙办事,我平白无故收人家的玫瑰花,这事……
说起来,周芳芳是大发麻将馆的一枝花。
何老板心里清楚:如今开麻将馆的,靠的是啥?一是方方面面的关系,二是人脉人气。不说别的,开麻将馆的,光金银街这条街上就有十来家,哪个老板不想把自己的麻将馆打理好?哪个不想财源滚滚?可事情往往不遂人意,有的麻将馆打牌的人少,有的人多,人多的明摆着就是财路广嘛。对于老板来说,说好听点,牌友是麻将馆的上帝;说不好听点,就是麻将馆的税源。像周芳芳这样温柔漂亮的女牌友,男人们见了就乐得屁颠屁颠的,打不打牌都愿意往人家身边个凑。若是稳住了一个芳芳,就等于稳住了十几个男牌友的心。我这麻将馆,如果有五六朵这样的花儿一直给招蜂引蝶,生意还发愁?她嘴上虽没这么说,心里却每天惦记着她能不能早点来。
开麻将馆的,不怕你一次两次的赢,就怕你不来。只要你常来,一切都好说。
周芳芳给田和平刚打完电话,何老板的电话就打进来了:“美女呀,到哪儿啦?……噢……噢,好,看见你的车了,给你把茶水备好,还是龙井吧?……好。”
听了这话,周芳芳心里暖融融的,麻将馆的台费不让何老板赚还让谁赚?说实话,她家门口对面,就开着一家麻将馆。那儿的老板好几次摆着个笑脸,邀她到麻将馆打牌,她都是笑笑,说,得给一个多年的好朋友捧场,不好意思。在近点的麻将馆玩,确实方便,但她觉得打牌还是和熟人在一块儿玩要好点,有说有笑的,开心解闷。如果和生人玩,单纯就是个打牌,一下午闷着个嘴,反正就是一个赌了,没多少乐趣。这样想着,她下车后款款地进了麻将馆。
何老板今年50多岁,半老徐娘,留着齐耳短发,办起事来干练老辣。她原先在市林业局工作,前几年办了内退手续。多年的办公室工作练就了一套阿庆嫂的本领,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她见周芳芳进了门,就笑盈盈地迎过来,一眼就看见周芳芳今天穿的是件新连衣裙,便很大方地支付着自己的夸奖:“芳芳呀,你看,这咖啡色的颜色把你显得更白啦。这粉红色的领子,衬得你的脖子白皙细长。哈哈,更让人待见了——快上吧,茶泡上了。”
“是吗?谢谢老板啊。”
“谢啥呀?要说谢,我得谢谢你每天来给我捧场。”
麻将馆的一层,是老年人的天下。现在,已经打开一桌100元的小锅。打小锅的这些老头老太太大多是中午在床上躺一躺,稍作休息,心里就想着麻将馆,早早来了。
拄拐的和没牙的一块儿晒太阳,驼背的找谢顶的在一起打麻将。
年轻人呢,嫌一楼的老头老太太打牌太慢。哼!这些人在一块儿打牌时,那股劲,没法说。就是打个风头,也要左瞅瞅右看看,锅里不见两个同样的风头就不打,在手里把牌给你能捏出汗珠儿来。
啥叫熬,啥叫耗?这伙老头老太太慢悠悠地打牌熬时光,为此做了最权威的注解。
年轻人一般是熬不过老年人的,惹不起,咱躲得起。于是,王八看绿豆,相看两不厌。一伙老头老太太凑到一块儿,悠悠地起牌,款款地打牌。像这样的小锅,大发麻将馆每天下午有那么四五桌,一锅台费才16元,也算是给何老板发财路上的拾遗补缺。其次是250元的,算中锅吧。重点是大锅,这才是大发麻将馆的主打业务。大锅是2000元一锅,每锅每人抽取两个点,一锅台费就是160元。这和小饭馆里卖面的一样,得分等级,小碗、中碗和大碗。打大锅的,往往是鸿运别墅里的那些小老板和大款。对他们来说,打小锅纯粹是挠痒痒,没刺激,要玩就玩大的,爽。
麻将馆里原先大多是耍50元的、100元的,最大的也就是250元的锅。远嫖近赌嘛。自从鸿运别墅开园之后,出出进进的人给大发麻将馆带来了好运,“锅”的数量增加了,“锅”的质量提升了,拉开了500元一锅的帷幕。
逢年过节,牌友们凑在一起。
这个小老板说:“过年了,咱高兴高兴!来个1000元的锅刺激刺激,咋样?”
那个大款来了劲:“行!谁怕谁呢?”
于是,1000元的大锅应运而生。过了年,过了正月十五,再过了二月二,他们的兴致仍然不减,这伙人照旧打1000元的锅。
上了贼船之后,谁都觉得自己成了贼,但谁也舍不得下船。
他们的理由充足而直白:“咋?打大锅输了,小锅能扳回来?”
这也和当官的没啥两样,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不能降。人的贪婪本性与干部体制如出一辙。
再过个年,他们又涨成了2000元一锅。
周芳芳上到了二层楼,见赵长胜和李贵宝坐在麻将桌旁,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啃手机”。
牌场上的“三缺一”,是牌友们火烧眉毛抓耳挠腮的事情。
听见脚步声,赵长胜和李贵宝几乎是同时抬起了头,见周芳芳来了,两人咧开了嘴巴。
“我的妈呀,救场如救火,加上老板,能开张营业了。”赵长胜说着扭头朝楼下扯着嗓子:“老板——上来!”
“噔噔噔……”何老板走上楼来。一上楼就笑着说:“吱哇个啥?我更着急呐。”
“你呀,你着急是着急收台费,我们着急是想早点玩。”李贵宝调侃着。
买凉粉的,每天光嫌天凉;开麻将馆的,总怕人少。
“对,对。你说的对。”何老板一连说了几个对。她知道,说软话也少不了身上的一块儿肉,话得顺上牌友们说,才能堵了他们的嘴。要不,就是抬杠,而没啥意义的抬杠只会浪费时间,损耗了人气。浪费时间则意味着少收台费,损耗人气则意味着自断财路。
几个人坐在麻将机前,丢风,调位。老板东风,赵长胜南风,李贵宝西风,周芳芳北风。
定了位置后,何老板用手按了一下麻将桌中央的按钮。透明钢化玻璃的圆框里呼啦啦地响着声,骰子在里面乱蹦乱跳。她看了看几位,满面春风地说:“老板坐庄,赢个元宝。”
赵长胜坐的是南风位置,想了想说:“嗬,咱南风,千刀万剐,不胡这头一把。”
李贵宝嘿嘿地笑了笑,有点儿不服气,表了个态:“东风吹,战鼓擂,坐在桌前谁怕谁?”
周芳芳没说话,静静地听着他们几个人贫嘴。
赵长胜瞭了一眼周芳芳,淡然地说:“看看人家芳大姐,低调,就知道个闷头赢钱。神马都是浮云,赢钱才是目的。”说完这话后,他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晃了一下。
周芳芳抬头看了一下赵长胜,笑了笑,也未吭气。
还没打了一圈,黑脸、瘦猴精等几个牌友稀稀拉拉地来了。
在楼下,服务员容嬷嬷根据他们的口味,给他们的专用杯里泡上茶,端上来放在一支麻将桌旁的茶几上,又给何老板这桌和黑脸他们那桌都端上一盘时令水果,一张桌上还摆了一盒中档烟。
坐下后,黑脸拿起个苹果在手里转了转,看看上面有没有疤痕,之后的目光便瞟了一眼正在打牌的周芳芳,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咋了,下午不来趟麻将馆,浑身上下就觉得没精神。日他……”说着“咔嚓”咬了一口苹果。黑脸真名叫巩二锤,在市城管队工作,长着一副黑圆脸。瘦猴精平时不叫他的大名,叫他黑脸。时间长了,麻将馆的人也跟着这么叫,他也不在乎。前一段,黑脸在街上动手打了个摆摊的小贩。事情闹大了,为了平息事态,队里就找了个临时工来替他顶坑,他暂且也不用上班,在家里躲躲这个风头,正好能消闲一段时间。
听了黑脸刚才的话,何老板的心仿佛掉进了蜜罐里。她扭过头来说:“黑脸,这事好办呀,每天下午来,每天不就精神啦?”
瘦猴精笑着看了一眼黑脸,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朝何老板说:“老板,你听他扯淡。他哪是来打麻将?每天呀,不来这里瞧瞧人家芳芳,心里就虚得慌。”
“哈哈哈……”
瘦猴精的话像在水塘里扔了块石头,溅起了人们的一片笑声。
黑脸没有脸红,不过,即使红了也看不出来,最多是茄子色。
周芳芳的脸上倒有点泛红。她扭过头来对瘦猴精款款地说:“讨厌。”然后抬起一只手来捂着嘴巴“嗤嗤”地笑。
“操!肚脐眼还嫌肚累赘,你不一样?”黑脸用手指着瘦猴精,不服气的劲儿,“球,咱俩,半斤八两,谁也不要笑话谁。”
“哎,老板,你看黑脸,啊,文明场所净说些脏话,垫张卫生纸把他捏出去!”
老板愣神,笑着看瘦猴精,不知说啥是好。
赵长胜扭过身来,从茶几上的纸盒里抽出一张卫生纸,朝瘦猴精递过来,“哎,给。”
黑脸看了看赵长胜,说:“这家伙……”说着弯腰脱下了拖鞋走过去,笑着说:“我拍死你,拍不死也熏死你。”
赵长胜伸出胳膊护着脑袋,半仰着身子,做投降样,“不敢啦,不敢啦。”
黑脸停住,扔下拖鞋穿上。
李贵宝说:“啊呀,城管家,厉害,职业病呐。”
瘦猴精朝赵长胜摆了下手:“谢谢老弟。算了吧,如果现在把狗儿的捏出去,还得再等别人。”
黑脸笑了笑:“瘦猴精,屌样哇,还捏我?看我把你捏出去。”
瘦猴精瞧了瞧黑脸,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后说:“吃惯的嘴跑惯的腿,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心里想东,嘴上说着西。嘿嘿,人家黑脸老哥也会弯弯绕啦。”
“人家芳芳嘛……”黑脸说着眼睛又往周芳芳那儿瞟。
“哎——哎。”这时,何老板扭过脸来说:“你俩斗嘴就斗嘴,别搅和上人家芳芳。”
黑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老板,你还别说,咱黑脸明人不做暗事,咱来这麻将馆,就是想多瞄人家芳芳几眼,心里滋润。哪天,哎,哪天人家不来这儿耍了,第二天……第二天我肯定不来。嗨,我家门口不远,就开着一家麻将馆,吃的喝的比你这儿强多了。”
瘦猴精来了个顺竿爬,“嗯,黑脸老哥这话不差。老板,你得好好捧着咱芳芳。唉——我说芳芳家老汉——不知上辈子积下啥德,娶了这么个美人儿。咱呢,咋就没这艳福?我算明白嘞,人这一世,咱算瞎活。你看路边的蚂蚁,找上半天也找不上口吃的,说不定啥时还让人给一脚踩了,多可怜。灶台上的蚂蚁,人家不慌不忙,每天混个肚儿圆。你们说一说,这活法与那活法……”然后学着小品《卖拐》里范伟的腔调:“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人们被瘦猴精摇头晃脑的样子逗乐了。
“瘦猴精,嗯?进步了,能看出问题来了。”黑脸把脑袋往椅子上一仰,好像不认识瘦猴精似的。他接着说:“市郊的李家庄,那些‘拆二代’,这几年发啦。你们知道人家年轻人想啥?”他竖起右手的食指,“一、离婚换老婆,把房子拆了后,再换一次。”又竖起中指,“二、赌博玩大的,白马放不下,到的是澳门。三嘛,吸毒。不知咋的,修公路时,他们提前听到风声后,连夜就把亲戚们招来,给钱,在地里插柳枝。修路的来折算时,得按树苗给人家算。有的更来劲,在院里连夜盖简易房,忙得热火朝天,到时候按住房面积算。现在,我有点后悔,前几年,咋没花点钱闹个李家庄的农村户口?如果闹下,现在发啦。唉,会打闹钱的,就是好猫。”
赵长胜说:“这些人的良心都让狗叼了,趁机坑国家。不知咋了,现在,勤劳的不一定致富,胆大坑人的,都他妈的发了猛财。”
“现在谁还管那么多。”瘦猴精叨叨着。
这时,李贵宝接上话茬:“刚才,我在手机上看了一篇文章,你们猜猜,南方的一个贪官闹了多少?”
“多少?”
“38个亿。喏喏!日他先人,不要说38个亿,我要有五个亿,五个亿啊!”说着,他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摇了摇那只皱纹里似乎还透着煤渣子的巴掌,“哼,孙子才来这儿打这锅,我得跑到澳门过过瘾。还有,澳门赌场里的小姐,每天在里面转悠,揽生意。哈哈,好看呐!”
“嗨,宝哥,你别没边没堰地瞎侃,饱汉不知饿汉饥。说一说,前几年开黑口子,你闹腾了多少?哪像我们,饿不死也撑不着。有时候也就是喝点革命的小酒,打打小麻将,混一天算一天吧。”黑脸看着李贵宝说。
听黑脸这么说,李贵宝心里稍微有点不高兴,伸手摸了把自己的连鬓胡,嘴里嘟囔着:“这黑脸,哪壶不开提那壶。”
“哎——哎——你们打麻将吧,都浪费时间啦,有这空儿,早打半锅啦。”何老板招呼着,他看见人们闲聊胡扯,闹得李贵宝多多少少有点不高兴,若是无事生非,闹个不愉快,耽误了打牌……想到这些,她就有点心疼。
“好,好。来,丢风,丢风。”说着,黑脸就招呼着瘦猴精几个人,“快点坐,给人家打工。要不,老板叽叽喳喳的。”
正在这时,楼下乱哄哄的。
二层楼的人都走到楼梯口那儿往下看。
一群老头老太太站在一张麻将桌前,围成个圈儿,手忙脚乱地忙着什么。
何老板愣了一下,赶紧走下楼去。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处于昏迷状态,他靠在椅子下边。有个老太太用大拇指掐着这个老头鼻子下面的人中穴位。
何老板着急地探下身子,“吆?咋啦?”
正在掐穴位的老太太说:“老阎头听口上了架后,我们就看见他的手不停地抖,我们也没当回事。刚才,他摸了一张牌,嘴里说了个‘七’,这七还没说完,身子就……就溜到桌下啦。”
听了这话,何老板心里一惊:老阎现在溜在地上,这事情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他儿子阎王爷肯定会找上门来惹事。想到这些,她也顾不上擦擦额头上冒出的虚汗,从兜里掏出手机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给120打电话。
这期间,楼上楼下的几十个牌友们都围过来,伸长脖子看着昏迷不醒的老头。那个老太太继续给阎老头掐着穴位。
阎老头躺在那里,一直没啥动静。
过了十来分钟,一辆救护车打着鸣笛风驰电掣地来了。“呜啦呜啦”的响声引来一群过往的行人围在麻将馆门前看热闹。
三个救护人员拿着担架急匆匆地走进麻将馆。一个人蹲下来,用听诊器在阎老头的胸口上听着。听了一会儿,说患者得到医院抢救。
几个年轻人七手八脚地打帮着救护人员,把阎老头放进担架里,抬着出了门。
何老板嘱咐容嬷嬷先跟着救护车到医院去。
容嬷嬷点了点头。
救护车又“呜啦呜啦”地走了。
黑脸从外面进来后,着着急急地走到那个麻将桌前,把阎老头的牌子翻起来看。这把牌没条,没饼(筒),没风,全是万。一把好牌呀!
这时,瘦猴精慢腾腾地从外面走进麻将馆来,手里拿着一张牌,嘴里叨念着:“这老头儿,人都躺担架上啦,手里还紧紧捏着这张牌。”
黑脸伸过手来说:“我看看呀。”
瘦猴精把牌递给他,漫不经心地说:“七万。”
“七万?怪不得!”黑脸说。
突兀而来的惊喜,实在有点儿让人承受不起。
听黑脸一惊一乍的,打牌的都围过来低着头看牌。看着这副好牌,人们的眼睛都有点直。
“好牌呀!打牌遇上一把这牌……”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个边七万。或许是定力不够,当他气喘吁吁地爬到龙套龙的顶峰,还没来得及感慨“一览众山小”时,激动得就先把自个儿晕了过去。这就像买彩票的人每天怀着极大的期盼,坚定着信念买了彩票,然后拿着刀子小心翼翼地刮开获奖区,却只见“谢谢”两个字,而这回铁树开了花,好不容易得个大奖,本该手舞足蹈了,彩票却一不小心弄丢啦。
龙套龙,两条龙,自摸翻番四条龙。这种牌在牌场上极为少见,往往是主人精心打造,可还未等宏伟的主体工程完工,别人的小茅屋早已竣工剪彩,时差较大。龙套龙这种牌型,一般是可遇不可求,没有时不能强求,遇到时不能放弃。一旦成功就是:三年不开张,开张顶三年。
多年来,国人面临的最大悲剧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价值取向的扭曲与崩溃。在许多人的眼里,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仅仅定位于是不是升官,是不是发财。于是,权与钱便成了生活的宠儿。只要你一做个官,满眼都是遂顺之象,满耳都是恭维之言,很少遇到婉拒的现象,很少听到说“不”的声音。只要你一发财,其实你的财与别人也没啥关系,并未惠及于他,即使你是个侏儒,你的形象在他人眼里刹那间变得伟岸起来。即使你是个绘画方面的门外汉,信手涂鸦几下,画个鸡蛋轮廓或几条弧线,你就变为“伟大”的画家,甚至有追随者肯花几百万元来购买这幅“旷世奇作”,原因大抵是你比他有钱,他得套套近乎。
阎老头这么一闹腾,麻将馆里乱哄哄的,牌友们有的抽烟,有的吃水果,有的喝茶,有的上厕所,有的担心阎老头能否在医院里缓过气来,有的则坐在一边,算计着这边七万如果往牌桌上一剁,自己得该出多少张(点)扑克牌……
看到这种情况,何老板急忙吆喝着大伙儿各就各位,继续打牌,刚才这一桌的台费就免啦,换个牌友重新开打。安排妥当后,她长叹了一口气,不过,一股阴云又罩心头,讲理的怕不讲理的,不讲理的怕不要命的,老阎的那个儿子可是金银街、白马市出了名的混混,名叫阎大蛋,有的人叫他“阎王爷”。如果这个阎王爷为这事上门来找茬,我该如何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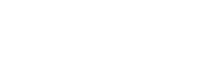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麻将馆
麻将馆
 重返1977黄金年代
重返1977黄金年代 月落星沉花未央
月落星沉花未央 青青陌上桑
青青陌上桑 何以解忧
何以解忧 绝世狂医
绝世狂医 烟花冷透两相忘
烟花冷透两相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桃运透视
桃运透视 总裁的新婚罪妻
总裁的新婚罪妻 鉴宝大宗师
鉴宝大宗师 神医赘婿
神医赘婿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龙狱之主
龙狱之主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一念神魔
一念神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