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馆》 章节介绍
岳峻得力之作《麻将馆》故事性很强,能够将读者带入其中。看过田和平刘黎明经历之后欲罢不能,很想直接看到大结局,下面是《麻将馆》第3章内容:第三章节外生枝就在大发麻将馆出现“边七万”一幕的时候,刘黎明和女牌友牛牛正在满眼碧绿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游......
《麻将馆》 第三章 节外生枝 在线试读
第三章 节外生枝
就在大发麻将馆出现“边七万”一幕的时候,刘黎明和女牌友牛牛正在满眼碧绿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游荡着,一路上打情骂俏,黏黏糊糊。
在茫茫的草原上,刘黎明想用放浪形骸的吼叫,驱逐久郁在心的块垒。这次,与其说他是离家出走,不如说是让妻子赶出家门。
说起来,刘黎明是麻坛老手。上高中那会儿,他就偷偷摸摸地学会了打麻将。那年高考他考上个大专,觉得不理想,他说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就让他爸给拿出些积蓄买了辆出租车跑出租,隔三叉五跟着一个朋友到外地鼓捣些二手车赚个差价。七八年时间,上午在街上跑跑车。下午的时候,就把出租车开到大发麻将馆的后院找个位置停放好,在麻将馆泡着,直至晚上十二点左右再开车回家。他老婆心疼他,劝他以后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别累坏了身子骨。他说没事情。这样一哄就哄了老婆多少年。
刘黎明今年四十二岁,一米八的个子,眉清目秀,浑身上下透着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一些女牌友也顾不上避嫌,有事没事总爱在他的身边坐着道啦。有的胆大的女牌友则干脆叫他明哥,说他比香港歌星黎明还帅。如今思想前卫的女性似乎不在意别人说三道四,我行我素,只要自己乐意开心,管你打雷闪电天塌龙叫唤。刘黎明自然明白这一点,加上他的嘴甜,你情我愿,拍拍打打,小毛病不断,大错误不犯,家里的小日子过得还甜甜美美。老婆呢,被他哄得一愣一愣的,还以为她的刘哥每天起早搭黑辛辛苦苦地为家里跑车挣钱呢。
打麻将时,他有个嗜好,就是谋算着谋个七小对、臭牌、清一色等大胡,一口想吃个胖子,可事情往往不遂人愿,虽然有时也能瞎猫碰见个死老鼠,风光神气一把,但过道里哪有那么多死老鼠等着让瞎猫逮呢?所以,他往往是胜少败多。他的脾气随和,打牌输了,不怨天,不怨地,不怨牌,输多输少也无所谓,女牌友叫他明哥,有的男牌友还叫他明爷呢。称他明爷还有个理由,就是他在炒股方面犹如神助,虽然打牌打得臭,但选股选得准。有时,他上午跑出租也是不慌不忙,能拉几个算几个,能挣多少算多少,不像别的手机那般东张西望,风急火燎。没乘客时,他悠悠地找个僻静的地方,点上支烟,掏出手机,一边抽着一边上网查看股市走向,分析大盘个股优劣,选准目标下手,每年能赚个百八十万。几年了,刘黎明没把这个秘密告诉老婆。隔几天,他就从股市里适量提点钱交给老婆,说这几天跑出租挣的钱,来个堤外损失堤内补。
牌友毛哥纳闷地说:“看人家明爷,从没见人家忙得东奔西忙,风风火火,每天稳悠悠地该咋就咋,身上却老有钱。”
下午,有时候打牌打得正在兴头上,刘黎明的手机响了,一看是老婆来的电话,便顾不上再“悠悠地”了,他急忙把牌住桌上按倒,说声“稍等片刻”,大步流星地往后院跑去。
看见他慌里慌张的样子,有的人掩嘴而笑。
刘黎明跑到麻将馆的后院,动作麻利地开门,发动着出租车,定定神,然后接通电话,慢悠悠地回话:“雅雅,么事情?……噢,知道了知道了……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哎呀,刚才跟打的的找零钱呐。噢,好了,就这吧,刚跑了趟郊区,现在正往市区赶。”说着按了几声喇叭。这一切摆平之后,他才容段时间吁了口气。
刘黎明急步赶回麻将馆,见几个牌友坐在椅子上边抽烟聊天边等他,有点不好意思:“呀呀,让大家久等了,来,继续打。”
女牌友牛慧芳朝他抛个媚眼,娇声娇气地说:“明哥,不要紧的,大家如果听口了,你多点几炮就行。”
“好的,没问题。”
牛慧芳出生那年,当时正热播电视《渴望》,可能受主角刘惠芳的影响,父母就给她起了个牛慧芳的名字。
看着两人热热乎乎,眉来眼去,黑脸在心里就喝了一坛子醋。牛慧芳现在是单身,他便用粗话撩逗着人家:“嗨,别说点炮,就是打炮,你明哥也没二话。嘿嘿。”
牛慧芳白了黑脸一眼,“没油烂腥(没意思)的,等会儿看我收拾你这个黑煤球。”
“收拾?正巴不得呢,瞌睡的遇上递枕头的,呵呵,咱就喜欢人家慧芳收拾,随时随地啊!欢迎!”
“ 等着,煤球。”
刘黎明打牌爱打个大胡,但大胡却不愿挨他的打。一年半载下来,输个十几万元也就顺理成章。打牌本来应视牌况而论,宜小则小,宜大则大。如果一味硬打,常常把手气挫伤,事与愿违。他打牌时,死打大牌,图过瘾,但炒股却灵活多变,并成为他“造血”的主要渠道。茶余饭后,有些炒股的牌友常常问他该买哪些股,他也不保留,和盘托出。一些牌友跟着讨了便宜,夸他是炒股高手。他说:“说来说去挣下点钱都转移到这麻将馆了。”虽然他年龄不大,但牌友们就这样叫他“明爷”。
自从开了歌厅,许多男人就成了连襟;自从开了麻将馆,许多陌生人就成了一家人,在麻将馆里同用一个勺,同吃一锅饭。
在麻将馆吃了晚饭,刘黎明,牛惠芳等几个人又凑成一锅。吃屎的闻见屁香,下棋的不嫌饭迟,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他们要打个新花样——锅带圈。
锅带圈,打锅时每人分发九十八个点,也就是扑克牌的每种牌样拿掉个2,这个2作为台费。在几圈内如无人塌锅(输掉九十八个点),那么四圈底就调风调位,接着再打,直至有人塌锅或八圈底时结帐。当初先人们发明麻将时,未曾想到麻将的继承者们费尽心机,推陈出新,演绎出诸多花样,丰富了麻将的内涵。国人沉迷于各自为阵的麻将到了无以复加,积重难返的地步。
刘黎明曾说:“如果人们拿出这种精神,莫说喊了几十年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八个现代化,也早就实现了。”
牛惠芳对坐在上首的刘黎明说:“明哥,今天下午我手气差,输了不少,你能不能少甩点碰。自己多碰点,给咱多赶几张牌? ”
“没问题,我大肚碰。”
坐在刘黎明上首的黑脸听了这话,有点不高兴:“大肚碰,专门截我,操。”
刘黎明说:“说说就说说,过下护花使者的瘾也不行?”
黑脸笑着说:“你要大肚碰牌,我就到厨房拿把菜刀,咱俩到外面练练。”
“不值,不值。都是来这里图开心,谁和你动手脚?”
“好!”黑脸说:“你当护花使者,显得我黑脸黑心黑肺的。谁不会怜香惜玉,卖个人情?你大肚碰,我就顶着你打,顺着人家牛牛。”
刘黎明没再吭声,牌在沉闷的气氛中开打。
牛慧芳这一锅打得特别顺手,似乎牌神护佑着她。第一把是坎八条的臭龙,庄家门清带自摸。在人们的吃惊之中,每人得出四十个点。第二把是碰碰摸,每人十六个点。
两把过来,三人各出五十六个点。
黑脸从桌斗里往出掏牌时嘟嚷了一句:“时间还没过半,任务过了半,这牌打得……别扭。”
刘黎明说:“大家都见了,我可没有大肚碰。”
黑脸无奈地笑笑:“正常打牌,不再顶着你打了。”
“顶着,顶着,半路别改道。”刘黎明看了眼黑脸,不高不低地说道。
牛慧芳下首的赵大毛说:“没办法,没办法,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人家手气顺啊。”
“哎,牛牛,刚才你去了趟厕所,是不是趁机拜了茅神?嗯?我也得去拜拜。”
“懒驴上套屎尿多。”刘黎明笑着说了一句。
黑脸站起身来慢悠悠地说:“咱也得拜拜茅神去,手气咋啦,这是?”说着,他看了看自己的那双手,又朝地上甩了甩,好像要甩掉什么似的。
麻将馆的厕所在楼下一层的一个拐角处。
黑脸患着糖尿病,打牌时就爱往厕所跑。他到了厕所后,挺着身子站在马桶前,脑袋呈45度角仰着,两眼茫然地看着块墙板,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一种惬意感油然而生:啥是幸福?幸福就是把着急办的事情利利索索地办了。比如撒尿,一直憋着,总不是啥好事,尿了才浑身轻松。明确了幸福的含义后,他的心情很爽,因为这趟尿,似乎尿出了一种体会,尿出了一种收获。当他提好裤子插着裤扣子往外走时,忽然又想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还没办,差点给忘了,这件特别重要的事就是拜茅神。这一段,打麻将的手气太差,他找了多种原因却一直没有找准,这着实让他苦恼、沮丧。人家牛牛就信这一点。于是,他又急忙转过身来,想了想,这事情不能马虎,得恭恭敬敬,得规规矩矩地站好,虔诚一些,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冲着前面的白瓷抽水马桶,马桶上有许多发黄的尿渍。他看了看,心想不管那么多了,拱着手,弯着腰,认认真真地拜了三拜。然后,他屏住呼吸,忍着刺鼻的气味,对着脏兮兮的马桶默默地祈祷:茅神啊茅神,求求你老人家发发慈悲,保佑保佑我黑脸的手气顺些,别人的手气差些;我赢些,别人输些。您老人家隔三差五就让我摸条龙,摸个七对,摸个臭碰碰,摸坏他们……
正在这时,厕所门板上响起“咚咚”的敲门声,接着传来瘦猴精的声音:“黑脸,你这熊,里面干球啥?这长时间啦,让我等得……憋死我啦!”
每天下午, 麻将馆里打牌的有六十多人,人们还断不了喝茶吃水果。为此,厕所也就成了麻将馆里的热门地带,尽管这厕所里没有窗户,通风不良,异味刺鼻。
拜完茅神后,黑脸才不紧不慢地拨开门上的插销,慢慢地开了门。他站在门前一动不动,用身体挡着瘦猴精,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慢吞吞地打着招呼:“呀!以为是谁呢?门敲得山响。猴老弟,尿急啦?老弟啊老弟,原来你老人家呀,现在亲自上厕所来啦!”
“废话。滚!”瘦猴精着得很,一只手捂着小肚子,像只虾。
“哈哈,别着急嘛。来,我给你续上——”黑脸唱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有完没完?滚开!”此时,瘦猴精浑身发抖,五官被尿憋得都扭曲得错了位。他的两只手捂着裆部,弯曲着身体,在原地不停地扭动着。他低着头看着地上,喊道:“快滚!”
黑脸磨磨蹭蹭地堵在厕所门前,欣赏着瘦猴精的傻样。他身体铁塔似的,丝毫没有挪身的意思,显得时间很富裕,自然也不值钱。“咋,紧尿了? 听人们说,这憋尿呀,啊,对身体……对身体可能……不怎么好,尿憋了的滋味说起来,说起来还真不好受哇,呵呵,你说,是不是这样,老弟?”他悠闲地好像逛大街。
“快!”瘦猴精实在有点憋不住啦,他抬起头来,眼珠子老大,恶狠狠地吼:“滚!”
瘦猴精真急了,黑脸才恋恋不舍地让开了厕所的门口。
此时,瘦猴精再顾不上埋怨啥,一头扎进臭烘烘的厕所里。厕所里传出瘦猴精的声音:“妈的……”
厕所里照明灯的开关在门外的木板上。黑脸想了想,伸手就把里面的灯关了。
厕所里立即蹦出一声:“啥熊?”
黑脸在外边傻笑着。
一股猛烈的水柱冲击着马桶的四壁,哗哗地……
听着里面的声音,黑脸用手捂住了嘴巴,嗤嗤的笑声从指缝间喷出,为自己恶作剧的成功演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对他俩来说,只要逮住机会,能坑一下对方就坑一下。回来的路上,黑脸想,活了这四十多岁,今天总算头次拜了茅神,就是不知道灵不灵?
不管啥时候,时间是最公平的,不紧不慢,款款地走着,但等待的时间总是显得漫长。
这时,赵大毛给刘黎明递过一支烟,说:“牌不顺,烟来薰。”他们两个人反正闲着也没事,点着烟一边抽烟,一边等人。
牛慧芳胡了几把牌,此刻正在兴头上。她把自己的右手伸开,呈刀状,一反一正地在牌桌边上来回磨着,“我把刀子磨得快快地,来个一吃三。”
看着牛牛磨刀的样子,刘黎明、赵大毛几个人都笑了。
这时,黑脸上了楼,乐滋滋地,“嗨嗨,咱下去也拜了拜茅神。现在就看看我的手气如何。”
赵大毛才回过神来,“怪不得,让我们在这里干坐,耗得人……球!”
牌局的发展,果然被牛慧芳言中。
重新开打后,牛慧芳依次是烂胡,吊白板摸、坎二饼摸……之后来个边三条的龙摸子。
一片惊呼。
老板何洁也闻声过来,笑着说道:“呀!牛牛厉害。东风第一枝,奖励!奖励瓶海飞丝洗发液。”
“ 牛慧芳,牛!”
大发麻将馆从开张以来,还是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上次是宝哥,何老板奖励了一盒软中华。何老板所谓的“东风第一枝”,即坐东风的人一鼓作气把其它三个牌友打塌。
这帐好算,不像平时数点子对金额那么麻烦。明哥,黑脸,赵大毛各掏两千元元,台费一百六十元元,牛慧芳一锅净赚五千八百四十元。
面对这种一人高兴,三人发愁的局面,黑脸挠了挠头:“哎?我刚才下去拜了茅神的呀,咋还不顶用?这……这……”
看着黑脸疑惑不解的样子,瘦猴精有点幸灾乐祸,“呵呵,一个,心不诚则不灵。一个,让你刚才堵门,让你再馊,还关灯!”
“哪儿凉快那儿去。”黑脸有点不高兴。
“说啥呢?行话没说错,三男一女,等于送礼。”在一旁观战的瘦猴精不痛不痒地敲着边鼓。
刘黎明看了牛慧芳一眼:“唉,掏吧。这是干啥呢?将近十天的出租收入没啦。昨天刚输了。我昨天就发过誓,今天不来麻将馆。”
瘦猴精接上刘黎明的话茬:“不来不来又来了,不打不打又打了,打了打了又输了,本想扳本谁知输得更惨了。”
“哈哈哈……”
黑脸若有所思,刚才拜了茅神,原以为手气会好些,结果还是输了。他对刚才拜茅神有点怀疑,却又不敢当众说出来,就岔开了话题,“哎,听人说,打麻将不顺的话,就去狐仙山拜拜狐仙庙,挺灵的。过两天抽个空,咱们去拜拜狐仙庙哇?”
“哈哈,旱路不通走水路呀。这黑脸,想开办法了。”刘黎明指了指黑脸,对大伙说。
黑脸哭丧着脸诉苦,“这一段手气臭,臭得很。去试试。哎,谁去?咱去吧,明爷?”他央告着刘黎明。
“去?去就去。”刘黎明答应了,“我这一段更臭呀。”
“你俩去呀?到时候如果有空,我也去。”赵长胜说。
瘦猴精、周芳芳看了看,说也有去的意思。
“刚好坐一车,我开车。”黑脸说。
其实,在麻将馆打牌,除极个别人之外,都是舒(输)家庄的部队。一开始,老板就预先抽了两个点,就像水桶下面捅了两个洞,一直漏水。你在外面接了一桶水,回到家里时,总的漏一些吧。漏了的,就是老板的台费。
麻将,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人们着迷,而人们则向它行贿大把的时间、精力与金钱。
晚上十点多,打牌的人们大多疲惫不堪,从下午两点半打到晚上十点半,除开晚上吃饭的半个小时,七个多小时的摸牌打牌,得眼观六路,得耳听八方,得排列组合……自然劳心费神,再有吸引力的游戏也难以抵挡瞌睡虫的侵袭。
麻将馆里,有输有赢的人们或低沉或愉悦地离开麻将馆,回到家的港湾抛锚停泊。
打牌结束的时候,牛惠芳看着刘黎明说:“明哥,捎我一程行不?”
“行,别说捎你啦,专程送你都没问题。”刘黎明卖着人情。
“还是明哥,不愧为是明哥。”两人相跟着下了楼。
看着他俩的背影渐行渐远,黑脸一边穿着衣服,一边悄悄地对何老板倒了一股子醋:“老板,你看……”他的嘴朝楼梯口那儿努努,“我看呀,这小牛想……想ko明爷。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坐下吸土,站起来吸风。嘿嘿嘿。”说着露出一脸的坏笑。
见黑脸乌七八糟地说了一通,何老板就白了他一眼:“你呀,尽说脏话,把人们想得都不正经。”
黑脸用手抖了一下挂在自己脖子上那条粗硕的金项链,“唉”了一声,声音中满是酸酸的味道:“回家吧,累啦。”
第二天早晨,刘黎明在餐厅吃着早饭。
这时,妻子贾雅丽接了个电话后,就急忙收拾东西,并催他快点吃饭,“先开车把我送到单位。今天上午,省里财务部的人到单位,要进行财务检查。科长刚打过来电话,叫早点去单位。”
听妻子这么说,他就加快了速度,仰起脖子把半碗粥灌了下去,放下碗后拿起半块馒头啃着就往门外走。妻子是单位的会计,平时上下班都骑自行车。
出租车出了小区的大门。
贾雅丽坐在副驾驶座上,她看见中控系统(两个座位中间)那儿放着条裤子,就顺手拿起来看了看,米黄色的,嗯?还是女式裤子,就问:“哎,谁的裤子呀?”
刘黎明扭头一看,妻子正盯着他。
小区门前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后面的车打着笛催,他就把车停在路边,有点发懵:“嗨,谁的?”
往常,他会说乘客不小心丢下的。他想,这可能是牛慧芳的,昨晚上车时她手里好像拿着个东西,是不是下车忘了拿?
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内,贾雅丽凭女人特有的敏感捕获了一只猎物:“说,谁的?”
“谁的?”刘黎明也不由得自言自语了一句。 此时,他真的有点儿糊涂,谁的东西丢这儿啦。
贾雅丽则坚信自己的丈夫在装糊涂,还人模狗样地装。
逼视的目光。车里寂静一片,只有启动的油门还在“嘟嘟”着。
他看了一眼妻子,只见揣疑已经把妻子平常那温柔、美丽的面庞扭曲得有点变型,有点怕人。她的眼睛涨得圆溜溜的,眼眶里,白色的成分陡然增加了许多,而黑色的那部分,正裹着两道寒光朝自己射来。
“噢……是这样的,昨晚回家时,可能……可能是一个女乘客下车忘拿了,就是这……”
从丈夫刚才略为一惊的神态到现在结结巴巴的回话中,贾雅丽觉得这事情并不简单。“说,到底谁的?”她的声音铿锵有力。
沉默。
妻子由刚才的揣疑发问刹那间变得平静:“好吧。今天上午,上级领导到我们单位检查财务,我也豁出去了,你不说实话,我就不下车,管他们检查不检查!”
贾雅丽发了狠心。
刘黎明清楚,妻子往日的平静就像山涧平潭,里面却包含着激流,只是平时看不出来。要命关头,崖头飞溅的瀑布就是最好的证明。想到这里,他惴惴不安地说:”昨天晚上,从麻将馆出来,捎了个熟人。可能是……是……她下车忘了拿她的裤子了吧。”
这时,贾雅丽轻轻地抖了抖那条裤子,问道:“晚上十点多,捎熟人?”
“昨天下午,不知咋的,突然就想买张彩票,试试手气咋样。买了张彩票出来后,听见隔壁麻将馆的哗啦声就进去了,调节一下节奏,一直坐在车里,窝得这腰……”说着,他用拳头轻轻地捣了几下自己的腰。
看着丈夫演戏,贾雅丽冷笑了一声:“说吧,每天下午,你到麻将馆打麻将,打了多长时间啦?”
“没有,没有,就昨天下午一下午。”刘黎明信誓旦旦地回答。
“还编?!告诉你吧,我有时给你打手机,总觉得你拖得时间很长,然后才接,总是静静地,没别的杂音,你还给我滴滴几下喇叭,功夫下得不小哇?”
听妻子这么说,刘黎明禁不住笑了起来。此时,他才发现,妻子这是哪来的推理判断,好像自己以前逢场作戏时,她就在旁边瞧着。“好,我实话实说,开车累了,有时就去麻将馆里坐坐,看看人家打牌。你不能一天让我窝在驾驶室里窝着。你看,我这腰窝的,窝成我脊椎病?”他开始以攻为守。
“还有脸说?行,这个不说啦,这裤子呢?”
刘黎明看了看那条裤子,“这……”
贾雅丽没再说话,转身打开车门就下了车。她一手搭着车门,冷静地说:“你走吧,我打的。”
“ 哎——”尽管他一再恳求,贾雅丽没有丝毫的犹豫,摆手叫住辆出租车,走了。
望着那辆绝尘而去的富康出租车,刘黎明咂巴了咂巴嘴,却没有说出啥话来,他知道,这回摊上事啦。
上午,他怅然若失地跑车拉客。中午快吃饭的时候,他给妻子打了个电话,作为蜗牛的触角来探探虚实,结果也被“你拔打的电话暂无应答”给碰了回来。算了,他把车停放在一个小饭店的旁边,进饭店后点了份葱爆鱼丝、一碗桃花面安慰了安慰自己空瘪的胃袋。出了饭店后,找个僻静阴凉的地方停下车子,午休一会儿。
停车不远处,一只流浪狗卧在一处阴凉的地方,吐着长舌,舌头一颤一颤的喘着粗气。树上爬着几只知了吱哇吱哇鸣叫着。它们合伙演奏着一曲歌,这夏天虽美丽,但热得人太难受……
睡得正香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破声,把刘黎明从睡梦中惊醒。醒了一会儿,他从出租车里出来,伸了伸懒腰,活动了一番窝屈的筋骨,嘴里蹦出一句:“日子过成球啦!”想来想去,都是那条该死的裤子带来这些骚臊味,把他原本安稳、平静、有节奏的生活給断送了。他看了看手表,时针指向三点半,想了想还是到麻将馆吧,没心情跑车。途中,看见马路边那座刚建起不久的招工大厦已经化为一片废墟。他纳闷着,这楼盖起来还没几天呀,怎么说炸就炸啦?
被炸毁的招工大厦裸露着乱七八糟的砖块、水泥、钢筋……
十几个戴安全帽的人正忙着在废墟四周拉扯安全隔离带,几台装载机呜呜地挥舞着前叉给大吨位的运输车装车。
一片树荫下,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手里吃着一支冰糕在嘴边吸溜着,吸溜了几口之后,想给旁边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尝一口,那个老头笑笑后又摆摆手,让男孩继续吃,他自己抽烟。旁边放着一辆小平车,平车上放着把铁锤。
刘黎明闲着没事,走过去给那个老头儿递了一支烟,老头儿看了看香烟是硬盒中华,高兴得擦了擦眉毛上的汗珠,沾满灰尘的手把眼眶额头变成个戏台上的花脸。他感激地看了刘黎明一眼,笑着说:“谢谢师傅啦。”然后舍不得抽,把那支烟夹在耳朵上。
刘黎明蹲下后问道:“老哥,这大中午的也不歇会儿?”
老头儿往废墟那边努努嘴,“趁人家拆这楼房,过来等等,等会儿过去捣些人家剩下的钢筋。”
刘黎明又指了指那个吃冰糕的小孩,说:“这是?”
“孙孩。上三年级。”
“这活也让小孩干?”刘黎明说。
“没法儿啊。再一个这段时间他们放假了,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他跟上出来耍耍。”
刘黎明看了看这个小孩,小孩的身上黑瘦干巴的,明显是营养不良。小孩穿着一双破旧的凉鞋,脚上的皮肤还有点皲裂。
老头儿看了看刘黎明说:“这孩儿命苦哇。唉,也不怕你笑话。他爸爸原先贩煤挣了些钱。有点钱就烧燥得不行,爱个赌博,打麻将、推条子,把挣下的钱都输了不说,还欠下许多饥荒,为了还债,就想把……”这时,老头儿扭头看了看孙孩,见孙孩在一边看地上的蚂蚁搬运小虫的尸体,就压低声音说:“想把孩子卖掉,儿媳妇说啥也不让,我们老两口也不让。儿子就和媳妇打架,媳妇气得不行,离婚走了。唉,儿子还是赌,不记。进去啦,进里面去啦。也好,让他在里面受受罪,我们也省心点。我们老两口就带着孩子从村里就来,来白马市找点活计干。小孩的奶奶给人家看门房,我前几年当环卫工,扫马路,好歹有个干的。去年,人家不让干啦,说我年龄大。现在,我只好捡点破烂,卖几个钱算几个钱,凑乎着过吧。”
刘黎明发现老头儿的眼眶里有点湿润,悄悄地问道:“儿子现在干啥?”
“出来没几天又进去啦。”老头儿似乎有种解脱的感觉:“咱管不住,有人能管住他。这赌博呀,害人!”
“噢——”刘黎明长长地吁了口气。“老哥,你歇歇吧,再等一会儿,捡些东西。”说着他又递给老头儿一支烟。
“哎呀哎呀!”那个老头儿一边接过烟后一边哎呀着表示感谢,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那儿,“你看。还夹着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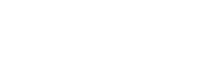
 麻将馆
麻将馆
 重返1977黄金年代
重返1977黄金年代 月落星沉花未央
月落星沉花未央 青青陌上桑
青青陌上桑 何以解忧
何以解忧 绝世狂医
绝世狂医 烟花冷透两相忘
烟花冷透两相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落入人海将你遗忘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木灵根觉醒后,种啥得啥带飞祖国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大雾四起,爱意藏匿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老公深夜错发消息后,我杀疯了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我都快渡劫期了,假千金还在争宠呢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师兄高抬贵手,宗门跪求你回头!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女总裁的妖孽保镖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萌宝:总裁爹地宠上天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天才兵王的幸福生活 超级保镖在都市
超级保镖在都市 第一狂婿
第一狂婿 总裁前妻要逃跑
总裁前妻要逃跑 桃运透视
桃运透视 总裁的新婚罪妻
总裁的新婚罪妻 鉴宝大宗师
鉴宝大宗师 神医赘婿
神医赘婿 天道有轮回
天道有轮回 一刀两断
一刀两断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九十九岁那年,我的福报来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相亲走错桌,却被女总裁表白了 横扫八荒
横扫八荒 开挂人生
开挂人生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哦吼!穿书后我成了男主他妈 龙狱之主
龙狱之主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后宫一线吃瓜,皇上你帽子绿了 一念神魔
一念神魔